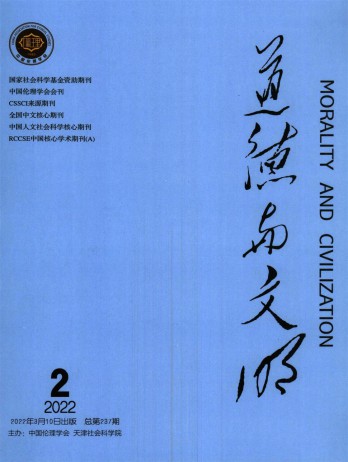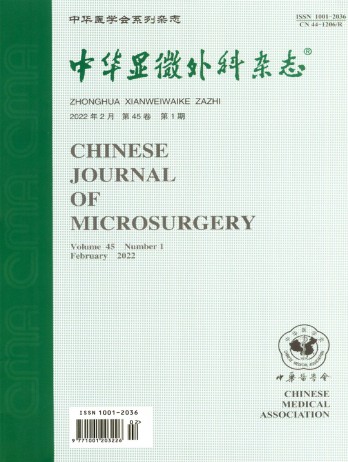道德與法治法律精品(七篇)
時間:2023-09-10 14:39:59
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道德與法治法律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關鍵詞] 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專題教學法;“幸福發展觀”;醫學院校
“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以下簡稱“基礎”課)是大學生德育與法制教育的主渠道。如何通過專題教學法,把大學生的德育與法制教育有機融合起來,構建一個“幸福發展觀”的“基礎”課教學體系,是我們北京中醫藥大學“基礎”課任課教師以實現大學生全面而自由的發展為教學目標的有益嘗試,通過專題教學法,凸顯人生幸福的價值取向,同時將教學體系融為一個道德化的法制教育和法制化的德育的有機整體,收到了良好教學效果,克服了當前“基礎”課普遍存在的“兩個頭”教學模式和“拼盤式”教學現象,以及“千人一面”的說教形象,提高了教學的吸引力、親和力和影響力。
在講授具體課程內容之前,我們把本課程的教學目的和教學計劃向同學們做了明確的介紹,并結合教材內容,強調培養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質和法律素質對自己大學生活和未來人生的重要意義,并向大學生具體闡釋了作為“科學發展觀”主體向度的“幸福發展觀”的具體含義。
“幸福是人們對現實生活的主觀反映,它既同人們生活的客觀條件密切相關,又體現了人們的需求和價值。主觀幸福感正是由這些因素共同作用而產生的個體對自身存在與發展狀況的一種積極的心理體驗。”[1]而幸福發展觀,就是以人類幸福、每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為終極目標的科學發展觀在人生觀和價值觀上的體現,它凸顯了科學發展觀的主體向度,即人的主觀感受與體悟。其中,幸福發展觀的核心概念有:“幸福感”,“國民幸福指數”,以及“每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
“幸福感是人們對自己現實生存狀態的一種正面或非常滿意的主觀感受。它主要由三種感覺構成,即生活和事業的滿足感、心態和情緒的愉悅感和人際與社會的和諧感。也就是說,幸福=美滿生活+愉悅身心+和諧關系。影響幸福感的因素主要有四個,即社會發展水平、歷史文化背景、個人社會階層、個人生存狀況和改善預期及其實現度。”[2]對于一個社會而言,如果將“每一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作為社會發展的基本原則,將人類幸福和人的全面自由發展作為發展的最終目標,那么,經濟的發展只是手段,而人的幸福和人的發展才是目的。所以,發展的終極目標不是物質財富的最大化,而是人類幸福的最大化。
“國民幸福指數”(GNH)首先由不丹王室于上世紀70年代提出,旨在推進政府如何為國民幸福謀福利,后來美國、英國相繼引入,進而應用到世界各國。從GDP到綠色GDP,再到人文指數HDI,最后到幸福指數GNH的提出,這種指數上的嬗變,反映了從經濟發展、社會發展到人的發展的路徑轉換和價值觀更新。有專家預言,在不遠的將來,幸福指數GNH將與GDP一樣重要,成為監控國家經濟社會運行態勢,了解人民的生活滿意度的有力工具,同時成為科學的政績考核標準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基礎”課的具體講授中,我們梳理出六個教學專題,通過專題講授,有機融合德育與法制教育的教學內容,實現了對“科學發展觀”主體向度的“幸福發展觀”的細化和分解。這六個專題的主題和內容分別是:
專題一:“新的生活、新的希望”,包括緒論(珍惜大學生活、開拓新的境界)和第一章(追求遠大理想、堅定崇高信念)的內容。首先從“什么是大學”講起,以大學生如何做人、做事和做學問為主線,把思想道德素質教育和法律素質教育有機融合起來,使大學生了解身上肩負的社會責任與歷史使命,幫助大學新生盡快適應大學生活,樹立新的學習理念,培養優良的學風,正確處理好自由和紀律的關系,要做一個動機與效果都向善去惡的大學生,在做好人和做好事上體現當代大學生的嶄新形象,成為有成熟思想、良好道德行為和明確法律意識的社會棟梁。在本專題中提煉出幾個教學案例,例如:“大學生的理想信念與權利義務”、“藥家鑫案的反思”等等。本專題突出“新”字,強調大學生活之新,在于孕育新的理想,幫助大學新生盡快適應大學生活,找到自己的生活節奏,樹立新的理想和新的奮斗目標。
專題二:“主義、國家、價值”,包括第二章(繼承愛國傳統、弘揚民族精神)和第三章(領悟人生真諦、創造人生價值)的內容。
首先從“什么是主義”這個話題入手,通過同學討論和教師總結,使同學們對主義、原則和理念等抽象概念產生濃厚興趣,進而提出并討論道德原則與法律原則之間、道德理念與法律理念之間的異同,使同學們真正認識到道德與法律在原則和理念的層面上具有十分密切的同源關系。其次,從“什么是國家”入手,通過理論探討和經典案例分析,使同學們從道德情感與法律這兩個層面更好地理解什么是愛國主義,怎樣做才是一個真正的愛國者。最后,從“什么是價值”入手,通過對人生真諦、人生價值和人生目的的講解和經典案例分析,使同學們樹立正確的價值觀和人生觀,自覺主動地把自我價值的實現與國家民族的命運機密結合起來,把主義與國家、價值串聯起來,用思想成就信仰,用信仰凝聚力量,用力量創造價值,用價值實現主義,用主義引領人生,用人生振興中華,做一個忠誠的愛國者,讓自己的人生更有意義。在講授“愛國主義的科學內涵”時,強調愛國是一個憲法規定的公民義務,危害國家安全罪就是對個人與國家關系的刑法調整;在講授“愛國主義與弘揚時代精神”時,我們強調創新需要知識產權等方面的法律制度的保護;在講授“做忠誠的愛國者”時,我們強調堅持民族團結、反對分裂的重要意義,并聯系《國家法》、《民族區域自治法》和《國防教育法》等法律內容,幫助大學生增強國家主權意識、民族團結意識和國防安全觀念;在講授“科學對待人生環境”中,強調《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對正確處理人與自然關系的意義和作用。
專題三:“私德與公德、人格與尊嚴”,包括第四章(加強道德修養、錘煉道德品質)和第五章(遵守社會公德、維護公共秩序)的內容。首先從“徳是什么”講起,講解道德的起源與本質、中華民族優良道德傳統的主要內容,以及私德與公德的區分,然后通過強調社會主義道德建設的核心和原則,深化榮辱觀教育、社會公德教育,提出踐行社會主義榮辱觀對維護社會公共秩序的重要意義,并通過介紹公共生活、職業生活和婚姻家庭生活中的相關法律規范和經典案例分析,闡明當代大學生恪守公民基本道德規范的意義和途徑,最終落實到當代大學生的人格誠信與人格尊嚴的養成教育中,將道德要求內化為大學生的自覺行為,使大學生養成尊重他人、恪守誠信的良好習慣和人格風范。在本專題中提煉出幾個教學案例,例如:“車輪上的道德與法律”、“當助人為樂遭遇‘釣魚執法’”、“當見義勇為遭遇‘過失殺人’”等。
專題四:“工作與家庭、親情與愛情”,包括第六章(培育職業精神、樹立家庭美德)的內容。首先從“孝是什么”講起,闡述家庭美德與職業道德的基本要求,通過介紹職業生活和婚姻家庭生活中的相關法律規范和經典案例分析,使當代大學生樹立正確的創業觀、事業觀、愛情觀和親情觀,為將來處理好工作與家庭的關系,以及親情、友情與愛情的關系,打下良好的基礎。在本專題中提煉出幾個教學案例,例如:“小悅悅事件的反思”、“融合在道德與法律的護佑下選擇你的真愛”、“‘大義滅親’的道德爭論與法律演變”等。本專題強調“孝”字,幫助大學生牢固樹立“百善孝為先”的觀念,將中華民族的優良道德傳統(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有吾幼以及人之幼”等)薪火傳承、發揚光大。
專題五:“自由與民主、權利與法律”,包括第七章(增強法律意識、弘揚法治精神)的內容。首先從“法是什么”講起,闡述法的起源和實質,通過介紹我國社會主義法律精神、社會主義法治觀念和經典案例分析,使當代大學生增強法律意識和國家安全意識,樹立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義和權利義務觀念,培養法律思維方式,自覺維護法律權威,做一個知法懂法守法的合格公民。在本專題中提煉出幾個教學案例,例如:“自由與民主的緣起”、“權利與法律的演變”、“這是正當防衛嗎”等。
專題六:“公民與人民、公平與正義”,包括第八章(了解法律制度、自覺遵守法律)的內容。我們首先從“公民與人民的概念和異同”講起,通過講解公民意識與為人民服務的理念,系統介紹我國憲法規定的法律制度和重要的實體法律制度、程序法律制度,通過經典案例分析,使當代大學生掌握基本的法律知識,增強維護法律尊嚴的使命感和責任感,為將來更好地參政議政、促進自身全面發展,打下堅實基礎。在本專題中提煉出幾個教學案例,例如:“我國憲法的歷程”、“知識產權糾紛案”、“行政法案例分析”、“辛普森殺妻案”等。
通過專題教學法,實現德育與法制教育的融合創新,可以有效解決醫學生面臨的社會義務、法制觀念、心理健康和人格理念等方面的現實問題,促進他們幸福成長、健康成才。因此,我們認為,將這種以“幸福發展觀”為價值取向,以“二教合一”為核心內容的專題教學法應用于醫學院校“基礎”課中,可以很好地落實“基礎”課的教學大綱和教學任務,實現當代大學生全面而自由發展的高等教學理念。
參考文獻
[1] 邢占軍.測量幸福—主觀幸福感測量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2] 樂正,邢占軍,鄭梓楨.從GTP崇拜到幸福指數關懷彰顯以人為本[J].南方日報,2006,6,23.
[3] 姜宏波.人的幸福指數評價及實現途徑[J].沈陽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1(157).
篇(2)
Abstract: Legal ethics in ancient China is a unique cultural feature in Chinese history. The merge of law and ethics is the obvious performance of feudalism in China. The article evaluates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he legal ethics in Chinese history.
關鍵詞: 中國古代;法律倫理化;利弊得失
Key words: ancient China;legal ethics;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中圖分類號:D9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4311(2011)25-0270-02
0 引言
中國古代法律倫理化是個漫長的過程。在中國四千年法制發展史中,中國古代法律經歷了夏、商、周時期的早期發展階段。在夏、商、周時期,法律以習慣法為基本形態,法律是不公開、不成文的。春秋以后,古代法律由習慣法向成文法轉變。到了秦漢時期,中國古代成文法法律體系全面確立,再經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的發展過渡,至隋唐,中國法制逐步完善、定型。宋元明清基本沿襲唐律的精神。從法律精神或法律指導原則方面來說,中國古代法律從漢代中期就開始了法律儒家化或稱法律倫理化的過程。法律倫理化的過程持續了八百余年,到隋唐時期終于結出了豐碩的果實,以《唐律疏議》的制定完成為標志,中國古代倫理道德與法律的融合過程,即通常所說的法律“倫理化”或“禮法結合”的過程基本完成。
1 中國古代法律倫理化的肯定方面
中國古代引禮入法,法律倫理化的表現學界論述較多,此不贅述。中國古代法律倫理化的出現,必有其歷史的合理性,值得肯定的方面可以歸納為二:
1.1 “明刑弼教”,有助于社會倫理秩序的強化 儒家理想化的基層社會是九族相親、鄉里和睦,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救,而教化齊同。[1]自漢至唐以至于明清,統治者治理社會的指導思想不外乎是德刑交互為用,法律一直是作為道德教化的輔助手段。漢代人鄭昌說:“圣王置諫爭之臣者,非以崇德,防逸豫之生也;立法明刑者,非以為治,救衰亂之起也。”[2]清人顧炎武說:“法制禁令,王者之所不廢,而非所以為治也,其本在正人心,厚風俗而已。”[3]清代人紀昀曾說“刑為盛世所不廢,而亦盛世所不尚。”法律倫理化,“明刑弼教”體現在立法活動中是把“三綱五常”、“尊老憐幼”、“親屬相隱”等倫理道德范疇的內容納入法律中,強制人們遵守,此即朱熹所謂的“以治之為之教,以明之為之刑”。
在司法活動中,“明刑弼教”最好的體現就是“禮去刑取”、“出禮入刑”、“春秋決獄”,以倫理道德原則去評判案件的情節輕重,罪行大小,起到了弘揚倫理道德的作用,達到了“弼教”。[4]法律倫理化在一定程度上使家庭“推財相讓”、“追行喪服”、“出居者皆歸養其父母”,邑聚相率,爭勵孝行,使社會倫理秩序得到了加強,有利于社會穩定。
1.2 執行方式比較溫和,易于讓人接受 在古時,“刑法不分”,“禮法”的執行手段和“刑法”的執行手段并無明顯區分。先秦之法,酷在重刑,嚴在告奸連坐。比如法家人物李悝的“窺宮者臏,拾遺者刖”、“議國法令者誅,籍其家及其妻氏”、“越城,一人則誅,十人以上夷其鄉及族”的立法和商鞅的“民人不能相為隱”的立法,都是“以刑去刑”,執法非常嚴酷。到了漢代,董仲舒提倡“春秋決獄”,而后西晉“準五服制罪”原則和北齊的“重罪十條”的實行,使得法律將倫理道德中的“尊尊”、“親親”、“容隱”等內容融入其中。一般說來,倫理法的執行手段是在“墨、劓、刖、宮、大辟”之外或“笞、杖、徒、流、死”五刑之外的。法律倫理化,以禮入法,使法律的執行更合乎眾人之情,法律的嚴酷程度減弱了。倫理化的法律在執行實施過程中,對那些正在“禮法”邊緣上即將脫出規范的人是一種溫和而嚴厲的警告,而對守“禮法”的人是一種表彰、鼓勵,對那些已經違反“禮法”的人來說,則是一次給其留了自新之路的有限懲罰,也不會逼著其“破罐子破摔”下去,比較易于讓人接受。
2 中國古代法律倫理化的弊端
中國古代法律倫理化塑造了中國傳統法律“依倫理而輕重其刑”的特征。在中國古代,確定罪的有無、決定刑的輕重,主要是依據倫理關系。在中國封建社會中,君臣、父子、兄弟、夫婦、長幼、尊卑、貴賤、上下,存在著巨大的社會差別。在法律上,同樣一種行為,由于不同主體實施,其法律刑懲后果決然不同。此外,中國古代法律制度的階級性決定其為加強帝王專制統治服務的本質,它著重是對尊者地位、尊嚴、利益的維護,少于對個人基本權利的保護。因此,中國古代法律,在封建社會發展的后期,其弊端也越來越明顯。其弊有三:
2.1 “為政在人”,“人治”傾向嚴重 由于古代東方國家是凌駕于對自身完全依附的社會之上的,推行的是“人治”主義的權力運行機制,凡此決定了國家所確立的法律,其價值旨趣完全受制于秉權者對法律的態度。[5]“為政在人”,“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有治人無治法。法不能獨立,類不能自行,得其人則存,失其人則亡。”以禮入法,法律倫理化之后,在中國的司法實踐中,更增加了司法過程中的人為因素。若負責司法審判的官吏道德高尚,以人倫原則辦理案件,則有利于社會秩序的穩定,但在司法實踐中受到以“春秋決獄”、“準五服制罪”,“忠”、“孝”等倫理觀念的影響,官員根據自己的理解對法律進行解釋,并以此為準進行判決,這樣“以禮斷獄”必然造成同事異議,獄犴不平,以至以禮壞法。面對人人皆非堯舜的現實,歷代王朝的決策者費盡心機,撤換“道德卑下者”,任用“道德高尚者”,并對官吏進行道德教育,期望他們倫理道德的凈化,但結果只能是周而復始的簡單循環,現實結果依然如故。伴隨中央集權的不斷強化,皇權不斷膨脹,帝王集軍、政、司法大權于一身,但皇帝個人精力畢竟有限,于是帝王身邊親信代掌詔獄,為宦官專權和特務政治提供了條件,于是,權力濫用越來越嚴重,腐敗不斷加劇。一次又一次的重復“為政在人”、“用賢去奸”之說也于事無補。“人治”排擠“法治”,社會缺乏以法律制約專制權力的法治精神。
2.2 維護以父權制為核心的不平等性 中國古代封建社會,“家”以父權為中心,“國”是“家”的放大,“家國同構”,“家”和由“家”構成的社會組織及“國”均存在著不平等性。在倫理化的等級分明的社會秩序下,“十惡”、“八議”、“準五服制罪”、“官當”等等內容,基本上都是抑卑幼奉尊長,家長、帝王等尊者的權威和尊嚴得到了全面支持和保護。古代社會法律內容的基本精神或實質是維護皇權、特權及極不平等的秩序。皇帝不僅是最高立法者,也是最高司法者,凡法律、法令均依皇帝的旨意制定,皇帝隨時的敕令均有法律效力。皇帝可以通過大赦或錄囚等方式行使審判權,同時享有死刑的最后決定權,充分維護了皇帝在國家中的最高地位。對于貴族官僚而言,法律規定了議、請、減、贖、當等極其周密的一整套制度,[6]使得貴族官僚享有高于常人的優越社會地位。對于國內百姓,法律嚴格區分良、賤,規定他們享有不同的權利、義務,為顯示社會等級的不同,還在婚姻方面加以限制,規定良、賤之間不得通婚。對于良、賤之間的相互侵害行為,適用不同的處罰標準。法律維護不平等的封建等級秩序,結果不僅造成了大量的司法不公,更是抹殺了卑幼的基本權益,使得整個社會在封閉與半封閉狀態下發展緩慢,大大落后于時代。
2.3 壓抑人性 由于在君主專制的封建社會時期,土地名義上為國有,而君主或帝王作為最高統治者,是社會財富的最高占有著,社會財產的最高所有權控制在君主一人手中。法律作為維護統治者利益的工具,剝奪了單個社會主體,即黎庶的應有權利。另外,封建社會的封閉性與自足性,導致人們所關注的只是自己的小塊土地,對國家政治乃至自身的政治權利漠不關心,并對自身的利益沒有保護、爭取的意識。這種在自然經濟基礎上建立的法律成為專制主義的有力工具,法律是為維護君主服務的,也就是為特殊的“人”服務的,是用來“治人”而自己處于法律的統治之外,[7]因此,中國古代法律造成了對非統治者人性的壓抑。由于君主專制的統治方式其本質就是對人性壓抑的專制主義,使得普通百姓的活動空間、活動范圍等收到了嚴重的限制,從而表現不出歷史的首創精神。
法律倫理化,“充當道德警察,干預日常生活”。[8]除了管人們的衣食住行,管如何說,如何寫之外,法律對人們日用生活之常幾乎無所不管,將人們箝制于名分等級的社會秩序中。
3 結語
綜上所述,法律倫理化,以禮入法有得有失。法律在司法實踐中確實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先秦時期“刑多而賞少”,加重輕罪的“以刑去刑”的苛法,[9]有助于維護家族和社會的穩定。同時,古代法律重視忠、孝,強調倫理,有助于社會倫理秩序的恢復。但是,中國古代法律缺乏“法治”精神,且以“人治”為主,法律內容的不平等性和對人性的壓抑延緩了社會歷史前進的步伐,這些弊端對當今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建設與發展有重大啟示。中國要構建和諧社會,應吸取古代法律有益成果,取其精華,棄其糟粕,以開放的視野和積極的心態學習一切民族的優秀成果和成功經驗,為己所用。
參考文獻:
[1]趙世超.中國古代引禮入法的得與失.《陜西師范大學學報》,2011,(1).
[2]班固.《漢書》卷23《刑法志》,中華書局,2002,(6):1102.
[3]顧炎武.《日知錄?法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324.
[4]范忠信.中國法律傳統的基本精神[M].山東人民出版社,2001,1(1):126.
[5]唐宏強.《國家與社會:傳統東方法律的運動機理》,人民出版社,2008,2(1):132.
[6]曾憲義.《中國法制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10(1):134.
[7]唐宏強.《國家與社會:傳統東方法律的運動機理》,人民出版社,2008,2(1):143.
篇(3)
[關 鍵 詞]傳統法官/實質性思維/形式性思維/職業化
中國歷史上一直沒有形成西方意義上的職業法律家。歷代所謂廷尉、大理、推官、判官等并不是專門的司法官員,而是行政官員——司法者只不過是作為權力者的手段而附屬于當政者。由于政治團體力圖阻止形式的法的發展[1](p.148),所以,我國歷史上不存在法律家階層,也根本不存在專門的法律培訓。受過文學方面的深造而中舉做官的人就可能兼為審判之事,另外一部分文人因自學律令而得以從事書吏、刑名幕友(師爺)或訟師三職(注:清代書吏無工資,主要收入靠陋規和舞弊,談不上研究法律,只是粗知律例條文。刑名幕友雖收入優厚, 但讀律的目的只在于佐東翁辦案,談不上系統地研究法律。訟師慫恿人打官司,以不正當手段從中取利,往往 無中生有,虛構或增減罪情,或誣告對方,包打官司,完全在暗中活動,既不在訟詞上署名,也不出庭辯護。 參見瞿同祖《瞿同祖法學論著集》,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413頁。),他們既無倫理根據,又無公眾口碑,既無經濟地位,又無政治前途。司法兼行政這項傳統制度一直延續到清末法制改革。因此,在我國歷史上缺乏推動法律前進的法律家階層,沒有“具主體性的”法律家[2](p.5)。因此,本文所稱的“平民法官”指非職業化的法官。
眾所周知,司法職業主義要求法官堅持思維的職業化,與平民的大眾化思維、政治性思維形成隔離;而司法民主主義則要求法官重視平民意見與利益,力圖符合大眾追求實質目標的要求。中國傳統法官的思維是一種平民式的追求實質目標而輕視形式過程的思維, 而當今中國仍然存在著這種傳統的延續,究竟如何看待這種傳統,恐怕不能一概而論。
一、中國傳統法官具有實質性思維傾向
這里所謂的實質性思維,又稱實質主義思維,指法官注重法律的內容、目的和結果,而輕視法律的形式、手段和過程,也表現為注重法律活動的意識形態,而輕視法律活動的技術形式,注重法律外的事實,而輕視法律內的邏輯。與其相對的是形式主義思維。 筆者擬借助于以下四對范疇來概括和分析中國歷史上傳統法官的實質性思維特點。
第一,傳統法官在法律與情理關系上傾向于情理。其斷案的基本方法是“衡情度理”,其斷案的普遍原則是“法本原情”、“原情論罪”,法官對法律與事實不作區分,而是把法律與事實糅合在一起,使每個案件的處理在規則的一般性和普遍性以外,考慮了事實的個別性和特殊性。這樣的事例很多,此舉一例:清道光末年江西潘陽縣有兩家兒女訂有婚約,男女兩家發生斗毆,事件本身已得到解決,但女方因此懷恨在心,試圖解除婚約,而男方不同意,訴至官府。女方父親揚言,如果女兒入花轎,將于當日自盡,女兒也表示即使一生不嫁,也不能嫁給父親的仇人。后來法官判該女終生在其父家守節,而男方則不得娶妻(《槐卿政績》卷六)。從國法的立場看,僅因斗毆事件而解除婚約是不能成立的,但從人情的要求看,不應該強求女子不情愿地嫁給對方,因而對兩者加以折中。
當出現法律與“情”、“理”相抵觸時,則堅持“舍法取義”的原則——因為“法律精神只是道德精神的劣等代用品”[3](p.112)。在古代中國,“法”總是處于“情”、“理”和“義”的下位(注:與日本文化進行比較會發現,中日兩國在理與法的相位方面有所區別,與中國不同,日本將“理”置于“ 法”的下位。參見[日]媾口雄三《中國的思想》,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22頁。)。
第二,傳統法官在法律目的與法律字義面前,傾向于目的。常常以抽象的一般原則作為依據,運用簡約、樸實的平民化而非職業化語言,依靠直覺的模糊性思維,而不是靠邏輯推理來探求法律的目的性,即使違背法律的字面規定也可以。這是反形式的思維。傳統法官在法律解釋中,可以超出文字的拘囿,根據目的需要進行“超級自由裁量”。例如東漢沛郡守何武判富翁遺書案。富翁有家資二千萬,養有一男一女兩個孩子。女兒女婿都很無賴,兒子年幼。富翁病重,寫下遺書:所有財產歸女兒女婿,只留下一把劍給幼子,并要求在兒子滿15歲才交付。到了男孩滿15歲那年,姐姐、姐夫仍然不給此劍,男孩只好到沛郡官府告狀。太守何武的判詞推定立囑人目的是為保護幼子,才將所有財產歸女兒女婿,否則會引起貪心的姐姐、姐夫謀財害命。何武主觀斷定“劍”乃決斷之意,應理解為待富翁兒子滿15歲必然要訴訟,重新分配遺產。最后判所有遺產轉歸兒子。法官說:“弊女惡婿,溫飽十年,已經是夠幸運的了。”可見,年幼的兒童與貪婪的成人在法官所理解的繼承法上的地位是不同的。法官在這里對繼承法顯然是從實質目的上作解釋,而不是從繼承法字面上去適用(《風俗通?佚文》)。這種案件在古代中國非常多見,在刑事司法方面也常常采用抽象的規定作審判依據。以抽象的規定作審判依據(注:以抽象的一般原則作為依據來判定犯罪,但清代所有的概括性禁律中可能是考慮到慎刑原則而沒有一條規 定死刑。有美國學者認為,刑部可能認為,司法機關不能因為被告的行為與語意模糊的概括性禁令類似,就將 其處死。參見[美]D?布迪、C?莫里斯《的法律》,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34頁。),從而遵守和維護了法律目的,這樣的案例如1819年的“奇成額案”:一個知恩圖報的學生打算自殺以跟隨他所尊敬的、已去世的老師。為了防止司法機關在他死后立案追查死因,他預先將計劃告知官府。后來他又改變了主意,被控困擾官府。查遍刑法典,無此項罪名。這樣的行為被認為是不得不追究和懲罰的。為了達到維護公務活動秩序的目的,刑部提出可根據一條概括性禁律量刑,即“不應得為”罪(做了不應該做的事),輕者笞四十,重者杖八十。所幸的是,奇成額因具有功名的身份,被允許納錢贖罪(《刑案匯覽》卷五四)。
第三,傳統法官思維中“民意”重于“法理”,具有平民傾向,把民意作為衡量判決公正與否的重要標準。而這種民意通常是平民意志。傳統法官具有不畏權貴的價值信念,比如“法不阿貴”、“為民伸冤”等等,被作為一種法官品格與職業道德(注:另外,《刑案匯覽》的190個案件中,涉及官吏犯罪的有20個案件,其中只有5人因其地位的特殊而獲得減 免。相反,在光緒七年(1881)一個案件中,刑部法官公開宣稱,由于被告具有官員身份,應對其嚴厲處罰。 參見[美]D?布迪、C?莫里斯《的法律》,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正因為這個原因,所以,中國傳統的狀子又呈現另一特點:并不是持明確的法律或權利主張,而是大篇幅地“敘述對方如何地無理、自己如何不當地被欺侮的冤抑之情”[4](p.214) (這是寺田浩明教授對中國古代訴狀的特點作了非常細致的研究后得出的觀點)。另外,古代法官的判決有注重文辭及情理并茂之特點,以博得民眾對“妙判”的好評,恐怕也與此有關。
對待貧民與富人的訴訟,采取對貧民傾斜保護以寧事息訟的策略,也體現了“民意”重于“法理”的特點。例如,據《折獄龜鑒》載,宋人王罕任職潭州時,民有與其族人爭產者,屢斷屢訟,十余年不絕。本來王罕可以將糾纏不休的告狀人斥為健訟而嚴懲不貸, 但這樣做只是“嚴”而達不到“明”。一日,王罕將此一族人召來堂上說,你們都是地方富戶,難道愿意長年受訟事煩擾?如今這告狀者窮愁潦倒,而當年析產的文據又不曾寫得清楚,所以屢屢不能決斷。倘若你們每人都稍稍給點錢財與告狀者,讓他們遠走高飛,豈不是斷絕了一切麻煩?大家按照王罕的話做了,訟事也就止息了。
“法不阿貴”的品格固然值得褒揚,但正是這一點又削減了法理在斷案中的分量。法官因疾惡如仇而不能平和對待當事人,不畏權貴則演變成借助于法律而達到劫富濟貧。由于法官自由裁量權較大,所以常常對平民有一定的惻隱之心。違法行為如果是小民百姓中常有的現象,也可作為減免刑的理由。例如據《刑案匯覽》卷七載,道光年間,周四在父親喪期娶周氏為妻,依法律既犯刑律“居喪嫁娶”條,又犯“同姓相婚”罪。但刑部批復說:“律設大法而體貼人情。居喪嫁娶雖律有明禁,而鄉曲小民昧于禮法,違律而為婚者亦往往有之。若必令照律離異,反而轉致婦女之名節因此而失。故例稱:揆于法制似為太重或名分不甚有礙者,聽各衙門臨時斟酌,于曲順人情之中仍不失維持禮法之意。凡屬辦此種案件,原可不拘律文斷令其完娶。”所以,刑部批復認為周四居喪娶妻是法官臨時斟酌,于律例并無不合。法官最后判決周四與周氏的婚姻成立。此處“鄉曲小民昧于禮法,違律而為婚者亦往往有之”,即是說百姓中常有的事,因此可以不作犯罪處罰。在清代,法官還可從法庭的旁聽人中選老成持重者數人以“體問風俗”[5](p.58),這也從另一側面反映了法官尊重民情習俗的平民傾向。
第四,傳統法官思維注重實體,輕視程序。傳統法官對糾紛的解決首先考慮實體目標,而非程序過程。古代有所謂“片言折獄”(注:孔子在評論弟子子路時說:“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子路名字)也歟?”(《論語?顏淵》)朱熹注釋 這段話時認為,“片言”是一半的意思,是說子路只要聽雙方訴說到一半就可以作出正確判斷。),作為對法官的最高評價,也是司法審判的最高境界。據《清代州縣審判衙門》第234頁載,清末同治年間鄞縣知縣段廣清所判“斗米斤雞”案,也反映了法官對弱者的傾斜。案情是:一鄉人進城不慎踏死店主雛雞一只,店主稱雛雞雖小,厥種特異,飼之數月,重可達九斤。依時價,一斤值錢百文,故索償九百錢。段氏問明底里,以為索償之數不為過,令鄉人遵賠。事畢段忽又喚回二人曰:“汝之雞雖飼數月可得九斤,今則未嘗飼至九斤也。諺有云:斗米斤雞。飼雞一斤者,例須米一斗,仿汝雞已斃,不復用飼,豈非省卻米九斗乎?雞斃得償,而又省米,事太便宜,汝應以米九斗還鄉人,方為兩得其平也。”店主語塞,只得遵判而行。
如將“片言折獄”的特點用現代法律語言來釋義,是指只要實體內容判斷準確,沒有正當程序也罷。古代程序依直覺思維進行,如“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注:“五聽”即辭聽、色聽、氣聽、耳聽、目聽,它源于儒家經典《周禮》,參見《周禮?秋官?小司寇》。)。沒有“對立面”交涉的正當程序,更多的是層級式的審判“手續”, 這種制度設置是基于一種信念:相信官級越高越能避免錯案。日本法學家滋賀秀三針對中國復審制程序說:“不待當事者的不服申訴,作為官僚機構內部的制約,通過若干次反復調查的程序以期不發生錯案的上述制度,可以稱為必要的復審制。這種制度在帝制中國的歷史中漸漸地發達起來,在清朝形成如此慎重,以至達到了‘繁瑣程度的程序’。律問題不是法庭辯論的對象,而是通過必要的復審制這樣一種官僚機構內部的相互牽制而達到正確解釋適用來解決的問題。換言之,這里不存在對相互爭議的主張由享有權威的第三者來下判斷的構造。”[5](p.9,12)
二、中國傳統法官實質性思維傾向形成的原因
中國歷史上的傳統法官為什么會形成這種思維特點?是什么因素導致這種實質性思維傾向的?筆者認為大致有三個原因,即文化、語言和組織三個因素。
從文化原因方面講,中國傳統文化有重內容、輕形式的特點(注:比如形式與內容作為哲學的重要范疇,在中國與西方美學中它們的關系是不同的。中國注重內容而輕視形 式,而西方則既注重形式又注重內容,甚至有時視形式高于內容。因此,有人稱中國美學為“內容的美學”, 西方美學叫“形式的美學”。在中國,藝術的形式沒有獨立自主性,而是為審美主體的思想、情感等內容服務 的。參見趙《西方形式美學》,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1頁。),中國的傳統法律也有重內容、輕形式(注:法律與情理的關系某種意義上說是形式與內容的關系。法律原本都和道德、政治、經濟、民意等事實因素 相互關聯,如果說寫在紙上的法律是形式,那么,其他所有道義或功利之事實范疇都是法律的內容。如果把情 與法、義與法聯系起來,那么,前者為內容,后者為形式。)的傾向,情況與中國文化的其他領域相似。就形式與內容的關系而言,中國法律觀與審美觀倒確實有許多相似之處。比如權利(義務)與程序的關系,正如中國審美中的“神”與“形”、“意”與“象”、“情”與“景”(注:“形神無間”出自陸時雍的《詩境總論》:“意象俱足”出自薛雪的《一瓢詩話》:“情景交融”出自方 東樹的《昭昧詹言》。)等關系一樣,前者為內容,后者是形式,它被當作手段,淪落為工具性的載體。這種思考或處理問題的方式混淆了兩種不同序列的事物,作為形式化預設的規則與作為這種規則最終目的的正義。這就導致不重視法律內在的合理標準,而是把外在于法律的合理標準(比如是否合乎情理和倫常,是否受民眾歡迎和樂于接受)作為追求目標(注:在西方法律觀念中,法律內部存在著自身的合理性標準,它不是于道德或情、理、義的標準,它是形式化 的,超越具體問題的。富勒所謂法的內在道德與法外在道德之區分,就是這個意思。美國學者艾倫?沃森說: “法律思維的理性建立在超越具體問題的合理性之上,形式上達到那么一種程度,法律制度的內在因素是決定 性尺度。”([美]艾倫?沃森《民法法系的演變形成》,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32頁))。這是一種反形式的傾向,被稱作“實質合理性”傾向。
中國的“情”至少有四層意思:一是指情感,它是與邏輯相對的概念;二是指道德意義上的“情理”,滋賀秀三將它作“常識性的正義衡平感覺”解(注:滋賀秀三認為這是“中國型的正義衡平感覺”,它是深藏于各人心中的感覺而不具有實定性,但卻引 導著聽訟者的判斷。參見[日]滋賀秀三《明清時期的民事審判與民間契約》,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3頁。);三是指情面,即俗話說的面子、臉面等;四是指與法律相對應的“事實”(注:“情”的原有含義是“情感”,但在法律文句中,它通常含有“事實”的意味,并且既有案件中的有 形的事實,又有無形的諸如當事人之間關系一類的東西。參見[美]藍德彰《宋元法學中的“活法”》,載《美 國學者論中國法律傳統》,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312頁。),接近于“情節”一詞。中國法律之所以與“情”難舍難分,大概有兩個原因:第一,由于法律與道德及宗教在性質與作用上具有某些共性,決定了法律思維與道德(宗教)思維也有許多相同或相似之處;第二,古代認為,法律與禮相比具有機械性,缺乏情感方面的內容,需要調和(注:儒家認為,中國古代的禮(其原始含義為儀式和典禮)給人們的生活帶來詩意和美感,為人們以社會 可接受的方式表達其情感開辟了渠道。參見[美]D?布迪、C?莫里斯《的法律》,江蘇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第15頁。)。所以,在法庭上人們(甚至律師與法官)不得不考慮某些情感評判。法律思維在這個問題上難以確立一個絕對化的基本原則,是“法不容情”還是“法本原情”,中國古代法基本上是“法本原情”的(注:中國法家的法律排斥“情”,而秦以后儒家的法律包容“情”,才使法律具有了“活力”。儒家化的 法律會根據“情”而改變刑罰。有學者認為,考慮“情”的程度,也就是法律真正合法和符合正義的程度。參 見[美]藍德彰《宋元法學中的“活法”》,載《美國學者論中國法律傳統》,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 第313頁以下。)。正是因為法律與道德等事實性因素在中國的過于密切結合,才出現法律的非形式化、非自治化,使得法律事業落后。
從語言原因方面講,傳統漢語語言有模糊性特點。嚴復在《名學淺說》中尖銳地指出,中國傳統思維的缺點是概念含糊、界說不清。他以“氣”為例,說“老儒先生之言氣”,有“正氣”、“邪氣”、“氣”、“厲氣”等,并慨嘆“出言用辭如此,欲使治精深嚴確之科學哲學,庸有當乎”?不但“氣”字,“他若‘心’字,‘天’字,‘道’字,‘仁’字,‘義’字,諸如此等,雖皆古書中極大極重要之立名,而意義歧混百出。廓清指實,皆有待于后賢也。”這種思維模糊性還具有極悠久的歷史,《論語》就是模糊性思維的產物。“《論語》不是以自然為知識對象而發現其規律,乃是依古代直觀的自然知識為媒介而證明人事范圍的道德規范。”[6](p.178) 中國法律的立法語言就有很強的概括性,例如《唐律疏議》中關于“故殺人罪”的“故”可解釋為兩種,即“故意”殺人和“無故”殺人。法律語言是一種技術形式,然而發達的道德意識形態抑制甚至扼殺了語言技術形式。
從組織原因方面講,歷史上中國法官基本上不屬于職業法官,而是儒家化的兼職官僚。與西方的法律相對自治相關聯的組織形式是——“法律的施行被委托給一群特別的人們,他們或多或少在專職的職業基礎上從事活動”[7](p.9)。古代中國執行法律的人不是訓練有素的法官,中國的制度設置中也沒有正式的法院,而是具有人文修養的行政官員和政府衙門。因而也就沒有把法律活動與國家的日常行政管理區別開來,也就是說法律活動沒有職業化。
正如梁治平君所言,“這種組織上的欠缺,自然導致對于過程的忽略和對結果的重視”。“法官的宣教職能以及作道德上安排的隨意性也就格外地突出。這里,過程同樣無關緊要,要緊的是結果,是社會的和道德上的效果。”[8](p.316) 法律既然與道德、政令等因素沒有分離,那么,它就不是“可計量”(注:這是韋伯用以比較中西法律傳統時特別強調的一個概念。)的法律,所以就不需要專門的法律職業和獨立的法律機構,不需要作為法律技術的解釋與推理邏輯,也不需要作為司法行為要件的正當程序。所以黃仁宇先生在評論海瑞時說過:“法律的解釋和執行離不開傳統的倫理,組織上也沒有對付復雜的因素和多元關系的能力。海瑞的一生經歷,就是這種制度的產物。”[9](p.135)
中國傳統法官把自己完全當作行政官(俗稱“父母官”,因而又是平民化的),把訴訟案件當作行政事務,把判決當作管理手段,把解紛結果當作合乎民意的政績。中國一直沒有出現職業化法官,在其審判過程中沒有形成職業化的思維方式,而是采用平民化、大眾式的思維方式,其實質在于用大眾思維來制作判決,力求判決能夠體現民眾的意愿,即民意取代了職業思考。這種傳統一直延續到現代中國。比如中國20世紀80年代以前的刑事判決書中有“不殺不足以平民憤”,就是一個典型例證。
三、中國傳統法官實質性思維的現代性問題
昂格爾與滋賀秀三說中國法處于與歐洲法對極(注:昂格爾以春秋末期到戰國時代為中國歷史上的大變革時期作考察對象,描述了那個時代“官僚制的法 ”的發生和發展。他指出,在中國不存在rule of law成立的條件。他把中國與歐洲兩個地區同時期的法律進行 比較,發現了它們的對立——“一種發展的出現與另一種發展的缺乏”。參見[美]昂格爾《現代社會中的法律 》,吳玉章等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91頁。滋賀秀三對昂格爾的“對極”作了解釋——與其他 非歐洲的法相比,中國法是離“法的支配(rule of law)”的理念最為遙遠的一極。參見[日]滋賀秀三《中國 法文化的考察》,載《明清時期的民事審判與民間契約》,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3頁。)的位置上,在法官思維這一點上也是如此。當代中國想要否定的這種實質性思維傾向,在西方卻出現了某些必要性。中國傳統法官的思維方式與后自由主義西方法官的思維邏輯具有某種異曲同工之妙。下面主要以清代判例為例來說明。
第一,中國傳統法官在正義問題上有實質正義的價值傾向,法官在法律解釋與法律推理中,不死摳法律條文的字面含義,這與西方現代法官在法律推理上異常地吻合。在現代西方國家出現一種趨向:法官從關注形式正義轉變為關注實質正義。 正如美國學者昂格爾在《現代社會中的法律》中所論述的:后自由主義社會中法律推理趨向目的性或政策導向,從關注形式公正向關心實質公正轉變[10](pp.193—194)。
古代的地方官為其職權所限,只可就笞、杖以下案件進行最后裁斷,這類案件事雖瑣細,卻不易斷得清明,處置不當,輕則聚訟不絕,重則傷于教化。不過在另一方面,法律賦予地方官相應的自由裁量權,又為那些有抱負的文官提供了施展才干的天地。他們依據法律,卻不拘泥于條文與字句;明于是非,但也不是呆板不近人情。他們的判決總是變通的,這正是對于法律精神的最深刻的理解。例如,《刑案匯覽》卷五載嘉慶十九年(1814)“張小許案”。張小許因伊弟將夏女毆死,聽從母命,頂兇認罪。法律規定,對于這種偽證、頂兇行為,應給予比原罪行所得刑罰輕一等的處罰。但張小許系迫于母親之命代替弟弟頂罪,因此,刑部在判決中說“這與普通人冒名頂兇者不同”,應于流罪上量減一等,處杖一百,徒三年。這種減輕處罰的依據并不是法律明文規定的。
第二,中國傳統法官的思維方式體現了現代法的特點——以模糊標準來處理糾紛。現代法不僅僅乞靈于嚴格規則,而且趨向于使用無固定內容的標準和一般性條款(法律原則)。以概括性規定或原則來量刑,這正是傳統中國法官在斷案實踐中表現的特點。
沒有法律明文規定,則適用一般性原則以達成合理的寬宥,例如據《刑案匯覽》卷四四所載嘉慶二十年(1815)“盧全海案”。被告盧全海之父被殺,盧因而將對方家中兄弟二人殺死。法律規定“一次殺死一家之內的二人,絞立決。若系一人所謀、一人所為,則該人應斬立決。盧全海依法應予斬立決,但是原審機關及刑部都建議皇帝對被告減刑處理,其理由是被告為報父仇而殺人。這里適用了一條沒有明文規定的抽象原則,即如果罪犯是為履行家庭義務而觸犯刑法,那么他應得到減刑處理。
第三,傳統法官具有平民意識,善于動用“情”的資源。雖然不符合職業主義的要求,但是體現了某種可貴的人權關懷和人文關懷。這種法官不但在自己的生活中嚴于律己,在對待社會弱者時,總是施以同情心予以傾斜保護,這恰恰與現代福利主義社會中的法律公平觀相吻合。比如勞動法對勞資糾紛、競爭法對經濟實力弱者的保護、消費者法對消費者的保護等等,都體現了實質主義公平觀。傳統法官像平民那樣對待法律與事實,至少它在個案中能夠實現具體的正義,很大程度上會受到贊成和擁護。比如明代法官海瑞說:“與其屈兄,寧屈其弟;與其屈叔伯,寧屈其侄;與其屈貧民,寧屈富民;與其屈愚直,寧屈于頑。事在爭產業,與其屈小民,寧屈鄉宦,以救時弊也;事在爭言貌,與其屈鄉宦,寧屈小民,以存體也。”
前述宋人王罕對該案件的處理就體現了平民性傾向,并且辦案的社會效果良好。故梁治平說,表面看同是依法行事,實際卻有深淺之分,真偽之別。執行法律某種意義上是一門藝術,必須創造。這時,法官的人格與識見就像藝術家的修養與趣味一般,是他們創造活動中最重要的因素[11](p.152)。
四、中國傳統法官實質性思維對現代中國法治的影響
現代中國法官仍然存在著這種實質性思維方式,這對于當代中國法治具有一定的危害性。
其一,中國傳統法官的實質性思維屬于非理性的法律思維,它導致法律術語貧乏,缺乏具有普遍性的嚴格的術語。這一點是中國古代法所欠缺的,因為中國古代法強調法律特殊主義而不是法律普遍主義,熱衷于律的細則化(注:瞿同祖先在分析中國古代法特征時指出了這兩個特點。他講到律的具體化,舉例說傷害罪,折人一齒 、一指,眇人一目,是何處分;折人二齒、二指,眇人兩目,是何處分,規定得十分具體。又如強盜罪、強盜 人數、持杖不持杖、是否傷人、得財多少、問罪不同。清代陸續的強盜條例竟有五十多條。瞿同祖先還指出: “著眼于犯罪的具體情況的種種差別,企圖使罪刑相當,立法也就越來越繁瑣,具體化的結果使得概括性的原 理原則難于發展。”參見瞿同祖《法律在中國社會中的作用》,載《瞿同祖法學論著集》,中國政法大學出版 社1998年版,第406頁。)。形式化要求法律的“普遍性”,包括通過一般性法律詞句——即通過較大綜合性與包容性的法律概念、術語——來表述法律內容,這些概念、術語是經過法律理性思維對法律現象進行抽象而生成的。其二,實質性思維導致的司法平民化,導致行外人士任意干涉職業法官的活動。判決被作為民意的載體,法官被當作民意的代表,因此,法院被當作政府的衙門,司法機關及其法官的獨立地位無法確立。其三,司法活動不講究嚴格的解釋與推理技術,更多地聽憑直覺與經驗,法律任憑官員任意解釋和自由裁量,因而導致擅斷和舞弊之風。其四,只考慮結果與目的,不考慮過程與手段,認為只要目的正當,結果合理,手段、過程是不必拘泥的;因而,把法律的程序通俗化為行政化的程序,即手續;程序的設定是為了權力的集中,沒有正當程序。其五,傳統法官總是將法律與事實糅合在一起,導致法律的確定性和可預測性很低。相對于法律,道德、政治、經濟、民意等都屬于事實范疇,傳統法官總是對法律與事實不作區分,即使是案外的事實也不作排除。當對這種事實的“情節”考慮是必要之時,法律無疑服從道德、政治、經濟、民意等事實因素。法律與事實不區分,必然出現權勢借用事實來壓法律,倫理、經濟等事實需要都成為否定法律的最好借口,打著“靈活性”與“目的性”的旗號,利用法的“穩定性”和“普遍性”的負面影響來否定法律的有效性、正當性,也就是費正清教授所指出的“破壞這樣的準則(指法律——引者注)是實際上求得方便的問題,而不是宗教原則問題”[3](p.109),“舍法取義”的結局是“有治法,而無法治”。所以,中國法官實質性思維方式,對于阻礙中國法治進程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在當今中國法律制度運行中,職業法律家尚未形成(盡管正在進行之中),法官與律師的職業化或專門化并不明顯。中國古代法官的非職業化傳統是有著深厚的歷史根基的,因而,在現實中國的審判活動中延續了一個現象:社會大眾與行家里手對待法律問題并不存在什么差異或隔閡。這聽起來似乎是一件好事,其實隱藏著危險。比如法官與老百姓異口同聲地說某犯罪嫌疑人是“不殺不足以平民憤”,這是非常可怕的。按理法官在程序中不該理睬“民憤”。法官的非職業化,會導致法律的非形式化,最終導致法律的非法治化。韋伯在分析“專門化”和法律形式主義傾向的時候說道:“法律朝反形式主義方向發展,原因在于掌權者要求法律成為協調利益沖突的工具。這種推動力包括了要求以某些社會階級的利益和意識形態代替實體正義;還包括政治權力機關如何將法律目標納入其理想軌道;還包括‘門外漢’對司法制度的要求。”[12](p.317)。這番話所講述的情況對于我們是如此地熟悉,好像是直接針對中國法治現實的。“非專業化”和法律的非形式主義是同一個問題的互為因果的兩個方面,由于中國傳統法律的非形式主義傾向,所以出現法官的非專業化;另一方面,正是因為法官的非專業化,才加劇法律的非形式主義傾向。
(本文據筆者在日本京都大學法學部的演講稿修改刪節而成)
[參考文獻]
[1] 韋伯。經濟與社會:下卷[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
[2] 邱聯恭。司法之現代化與程序法[M].臺北:三民書局(國立臺灣大學法學叢書),1999.
[3] 費正清。美國與中國[M].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9.
[4] 寺田浩明。權利與冤抑——清代聽訟和民眾的民事法秩序[A].滋賀秀三。明清時期的民事審判與民間契約[C].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
[5] 滋賀秀三。中國法文化的考察[A].滋賀秀三。明清時期的民事審判與民間契約[C].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
[6] 侯外廬。中國思想通史: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7] 伯爾曼。法律與革命[M].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3.
[8] 梁治平。尋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諧[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7.
[9] 黃仁宇。萬歷十五年[M].上海:中華書局,1982.
[10] Unger Roberto M. Law in Mordern Society-Toward a Criticism of Social Theory[M]. New york: The Free Press,1997.
[11] 梁治平。法意與人情[M].深圳:海天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