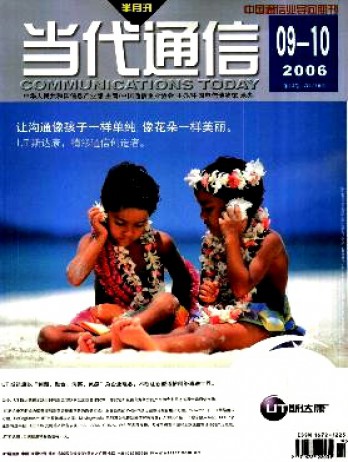通信發展史論文精品(七篇)
時間:2023-04-20 18:02:11
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通信發展史論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paringtoWesternEurope,therearesomeinstitutionalobstructswhenlabormarketsubstitutesforcommoditymarketinwhichsystemisdevelopedinMingandQingDynasties,whilethecostoffirmorganizationistoohigh.Itismoreefficientbymarketnetthanbyfirmorganizationthatthedivisionandspecializationisrealized.Itisthehighcostofimprovementofproductionimplementsthathinderthecapitalcontrollingdirectlyandmanagingtheproducingcourse.Thereisuniversalsignificancewithhistoricalrationalizationunderthephenomenonnotonlyinindividualindustryorindynastichistorythattheoperationsaretypicallyintheformofputting-outsysteminthespinningandweavingindustriesinMingandQingdynasties.
市場網絡或企業組織:明清紡織業經營形式的制度選擇
提要:企業是否替代市場,是各自的交易費用與效率比較之下的制度選擇。與西歐經驗相比,明清商品市場體系發達,勞動市場替代商品市場存在一些制度,企業組織的內生交易費用較高。分工與專業化的實現,通過市場網絡聯結比通過企業組織安排要更具效率。生產工具與設備改良的高成本,阻礙了資本對生產過程的直接控制與管理。以散工制為典型的明清紡織業經營形式,不是個別行業與某一斷代的現象,其歷史合理性具有相當的普遍性意義。
關鍵詞:市場網絡,企業組織,交易費用,明清紡織業
一、企業替代市場:一種制度選擇
企業替代市場,是制度經濟學的核心命題之一。市場規模的擴大,促進專業化和勞動分工,進而引起交易費用的增加。這是指專業化和勞動分工的程度越高,從生產過程到消費過程的交換的次數也越多,從而交易費用上升。經濟組織的變遷旨在降低這些交易費用,提高經濟效益。在科斯(1994)看來,企業是一個交易場所,在其中市場機制受到抑制,轉而由權威和指令來完成資源配置。也就是說,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市場中的交易成本越高,通過企業來組織資源的比較利益就越大。
科斯命題得到不少學者的闡發和深化。張五常(1996)認為,企業替代市場,從根本上來說就是勞動市場替代商品市場,因為一個企業組織的核心問題,實際上是對勞動力的雇傭、配置與管理。這有助于考察企業組織變遷中的交易費用,諾思(1994:230-231)也說,既然科層組織的縱向一體化意味著要以要素市場替代產品市場,那么,一個關鍵的決定性因素將是組織要素特別是勞動力市場的費用。企業在產品市場上減少了一系列交易,同時往往在要素市場上增加了另外一些交易。
另一些學者著重管理體系的特征進行了分析。錢德勒(1977:7;11)認為,當管理體系能夠比市場機制更加有效地配置資源與產品,協調許多業務單位的活動,并減少交易費用時,近代企業就應運而生了。德姆塞茨(1999)從管理成本的角度提出了與科斯命題相對應的企業存在理由的命題: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管理成本越低,通過企業來組織資源的比較利益就越大。換言之,如果市場交易成本超過管理成本,企業就會替代市場來實現利潤最大化。
除了通過替代市場降低交易費用外,企業組織[1]擴大的另一優勢是單位商品的生產費用下降,效益增加,這是其規模經濟所帶來的。產品批量生產越多,單位產品所耗費的生產資料越少,成本下降。同時,正如阿爾奇安和德姆塞茨(1999)所指出的,團組生產的生產率帶來了經濟效益的增加。這一點馬克思也曾作過論述[2]。
企業組織的優勢是有代價的,也就是組織變遷過程中將產生形成新的交易費用,可稱之為組織的內生費用。如果這種新的交易費用抵消了它所降低的原交易費用和生產費用,特別是所預期的或能帶來的收益與效率不足以補償這些費用,那么企業組織的優勢就得不到發揮。這些新的交易費用主要是,組織中規則的遵從、考核與執行,團組生產中需要監督來減少逃避與欺騙行為,而且如諾思(1994:43)所指出的,專業化和分工程度越高,從最初生產到最終消費者的整個生產環節也就越多,考核費用也就越多。此外,廠房、設備等也將帶來相應的費用。通過市場與通過企業組織,各自的交易費用與比較優勢,將決定制度選擇。
市場的功能不僅能有效地配置資源,還能尋求有效率的專業化水平和分工水平,發現有效率的制度安排,促進企業組織的改善。考之中國傳統社會,市場已發展到相當的程度,然而企業組織卻并未隨之發生較大改變。哪些環節存在障礙?為什么發達的中國傳統市場不能催生出近代企業組織?這是一個國內外學界廣為關注的重大課題,以往不少研究成果牽涉到與此相關的各種問題,尤以吳承明(1985)、方行等領導的資本主義萌芽研究、李伯重(2000)江南早期工業化研究最為突出,為進一步的探討奠定了堅實的理論支撐和實證基礎。
交易費用理論的要點與主要用途是,通過比較交易成本與管理成本的大小,得出組織選擇的結論(德姆塞茨1999)。這也是本文的基本出發點。本文以明清紡織業為重點,主要考察通過市場網絡聯結與通過企業組織兩種形式,在交易成本與效率方面有哪些差異,并通過與西歐中世紀及近代初期特別是英國經驗的比較,在較廣闊的歷史背景下對這種制度選擇進行分析,不局限于紡織業與市場本身,而是從傳統經濟與社會結構中探索其深層原因與演進源流。
二、企業組織的成長歷程與產業經營形式
從歷史實證看,企業組織的形成,一是商人資本在向生產領域逐漸滲透的過程形成的,二是商人、農場主、莊園主直接投資工業,都可能形成縱向一體化的組織,三是小生產者成功地擴大規模,雇傭工資勞動者,自己專事勞動的控制管理與產品銷售。第三種情形本文從略。第二種情形,在傳統中國與西歐中世紀,因主導性經濟組織的差異而呈現不同的歷史狀貌。西歐中世紀的莊園是占主導地位的經濟組織,具有較強的生產、交換與消費功能,個體農奴家庭對莊園的依附性較強[4],新型企業可能由莊園主蛻變而來。既然莊園主在種植商品性作物出售方面具有優勢,既然領主會開設市場吸引商人,他同樣可以利用自己的土地、勞動力集中的優勢,直接從事商品生產或工業制造[5]。在中國,地主承擔的生產組織功能越來越弱化,租佃制下個體小農獨立經營則越來越成熟(龍登高1992b),明清時的押租制、永佃制強化了這些趨勢。經營地主雖然存在,但始終都是次要的形態。地主兼商人直接建立的企業組織同樣影響有限,明清時主要在采礦業、伐木業、池鹽海鹽業、航運業、農產品加工業等領域中出現(吳承明1985)。
我們重點考察一下商人資本向生產領域滲透進而形成企業組織的情形。隨著市場的擴大,商品的制造與消費在空間上和時間上的矛盾加劇,對于商品生產者而言,作為生產時間扣除的商品銷售時間,作為勞動資料扣除的商品流通費用,都逐漸增多,也就是其交易費用提高。聯結產地與市場、聯結生產者與消費者的距離增加,鏈條拉長,環節增加,商人資本在其中的作用增強,逐漸向生產領域滲透。
在市場預期收益的促動下,商人向小生產者預付生產成本,進而為了保證商品質量與數量,商人向生產者提供原料,委托加工,包買產品。商人通過原料與成品兩個環節,進行產品質量監督,也進行必要的加工、包裝等環節,實際上開始涉入生產管理。進而提供生產設備,往往是生產者為償還債務等原因而將設備抵押給商人,或者是商人提供更具效能的設備——設備越復雜或越昂貴,資本家的控制就更快和更完全。此時資本幾乎支配了生產領域,但工業制造還是處于分散狀態。至此大體相當于分料到戶制,或吳承明(1996)所譯之“散工制”(putting-outsystem),都是依托商品市場建立相應的組織體系,但還不是依托勞動市場。此時商人資本也已兼有產業資本的要素。最后,制造者被集中到商人開設的廠房之中,這就是手工工場。當設備由機器構成時,手工工場就成為現代工廠。
中國存在這一現象,卻很難看到一個完整的歷史進程。宋代出現了商人預付資本包買產品的現象(龍登高1997:余論),明清時發料收貨的包買主逐漸增多,清代中期被稱作帳房的包買商在江南大中城市的絲織業中達到全盛,支配了當地的絲織業生產。有的帳房自設機督織,形成手工工場(范金民1995:220-223)。在其他工業中也有類似情形,如江南棉紡織業中,商人建立的布號,通過“包頭”(坊主)控制著眾多的小型染坊和踹坊的生產,經營市場廣闊的青藍布營銷(徐新吾1992:55)。布號進行嚴格的質量控制,形成自己的品牌,如益美號在200年間暢銷不衰,獨立小生產者按照布號制定的產品質量標準進行生產,可以說被置入一個大商業組織影響之下的生產單位(李伯重2000:82)。
分料到戶制,在英國的都鐸王朝和斯圖亞特王朝,因國內外市場需求的擴張而發展。它以生產任務的不斷分離為特征,迫使制造者擴大生產,改善生產方法,進而商人組織管理生產。16世紀,呢絨商安裝幾架織機雇傭短工來織,或者出租織機,無數小工匠面臨慘重的競爭。亞當·斯密時代,擁有三四百人的以水力為動力的工廠,英國約有二三十座(MarkBlaug,1985:37)。數量雖然遠遠比不上小企業之眾,但16世紀的英國毛紡織業向幾個富有的呢絨商手里集中,對傳統的手工業組織形成了威脅,都鐸王朝議會因而下令禁止商人的這類行為,以免傳統小生產被其吞沒或毀滅。大呢絨商約翰·溫奇庫姆經營的企業中,織工、學徒、梳毛工、運轉卷線桿和紡車、揀選羊毛、剪毛工人、整飾工、漂洗坊、染坊等,通常各有工人200名,少則數十名,共計達1200多名。這個數字顯然太夸大了,但可靠的是,約翰·溫奇庫姆的企業,在組織形式與通常的工業形式不同。至工業革命前18世紀前期的英國,各種工業已高度集中起來。
從分料到戶制向企業組織的變遷,在諾思(1994:第12章)看來是一個自然演化的過程。分料到戶制實際上是一種“原始企業”。商人業主試圖在制造過程中的每一環節中保持穩定的質量標準。實施質量管理所需成本的費用,在整個制造過程中保持對原料的所有權以考核質量,低于在生產過程的連續階段中簡單買賣所需成本。中心車間實際上更進一步,是更大的質量管理,而能在整個生產過程中直接監控質量是工廠體制發展的前兆。這也是為什么不簡單地用一系列市場交易而用一個中心制造商來雇傭勞動的原因。
然而,另一方面,對于商人而言,工業不過是一種商業形式而已。他們只考慮買賣差價,為了增加差價,他們利用個體工匠面臨的資金不足與產銷脫節的困難,控制原料,繼而控制設備,乃至工業廠房。他們是以商人的資格來掌管整個生產的。如果不需要控制原料、設備、廠房就可以節省費用并獲得更大的收益,或者這種控制同時帶來成本與風險,他們就不需要這樣做。實際上,無論是散工制下的市場網絡聯結,還是企業組織,都是一種產業組織形式,是基于交易費用與效率比較之下的制度選擇。
企業組織變遷過程中內生交易費用的產生,主要存在于三個方面。一是勞動市場替代商品市場過程中交易費用的變化,也就是企業科層組織的管理成本與市場交易費用之比較;二是生產資料的集聚尤其是設備、廠房等固定資產的生產費用與效率之比。三是分工與專業化的實現,通過市場與通過企業組織的區別。
三、勞動市場的交易費用:企業組織的管理成本
既然企業組織的形成過程就是勞動市場替代商品市場的過程,那么企業組織與勞動市場的發育程度等緊密相關。這一過程中所產生的內生交易費用主要是,勞動力的獲取與配置,勞動力的技能訓練,勞動力的管理,如組織內規則的遵從、考核、執行與監督等,當然還有勞動力的工資。如果要素市場發育不完善,那么,以要素市場替代產品市場的企業預期就低,而勞動力的管理成本則較高,企業組織的交易費用高。早期勞動力市場,還與經濟組織中勞動者的狀況、雇傭勞動力的來源等相關。
西歐中世紀的自由勞動力,最初來自莊園中分溢出來的人口。自走出莊園之時,大體就切斷了與土地相聯系的臍帶。因為農奴個體家庭經營較強地依附于莊園主,一旦脫離莊園,他們難以自我重建獨立的農業經營,除了進入工商業外幾乎別無出路,這是勞動力市場發育的重要原因。在英國,更有利的條件是16-18世紀的圈地運動,凡進行了圈地成立了大規模牧場之處,需要的勞動力大大減少。出賣了土地的自耕農和沒有工作的雇工都只能離開鄉村,涌向工業與城市。通常認為,到18世紀中葉,自耕農已大體消滅。在機器競爭尚未最后摧毀家庭工業之前,勞動力的集中就在進行著,勞動力市場漸趨發育。
中國的主體勞動者自耕農、半自耕農,與西歐的主體勞動者相比,具有更有效的產權制度支撐。中國的個體小農經營,不僅具有獨立性,而且當其再生產過程中斷后,比較容易恢復,或易地重建。因此,勞動力與農業的臍帶難以割斷,在工商業中被雇傭的勞動力始終與土地或農業有所關聯。另一方面,個體小農家庭通常都卷入工商業,或作為副業以補農耕之不足,或成為工商業專業戶獨立經營。
進入企業的工人大體有三種類型。第一種擁有土地或農業作為基本的生存保障,進入企業就像當作副業一樣以尋求更多的收入,他會根據收入的多少與農活的季節隨時退出企業。第二種是從事手工業時缺乏生產商品的物質資料,把勞動力賣給企業主,他希望而且有可能接受企業主的生產資料,以獨立生產的方式為企業主工作。這就是散工制下的工匠,有點類似租佃制的個體小農。第三種是工人的勞動力如果不出賣給企業主,就得不到利用,就會無以維生。明清中國的勞動力市場中,尤其是熟練工匠,基本上屬于前兩種,第三種即一無所有的自由勞動力很少。這些勞動力,或者擁有土地作為最低生活的保障,或者具有獨立經營的強烈意愿與市場機會。企業主雇傭工人與管理,對工人的行為約束的考核與監督,將需要付出較高的成本。明清江南地區,外來勞工難以約束,滋生事端,常見于記載。
諾思(1994:190)分析考核費用時,還專門考察了在缺乏有效的意識形態約束時,約束行為和考核費用就會非常之高,致使新的組織形式無法生存。這也就制度經濟學所強調的習俗與慣例的影響,中國的個體小農家庭獨立經營的制度具有悠久的歷史,意識形態積淀在深厚的社會土壤之中,獨立經營的價值取向很濃,這也影響到勞動力市場的發育。邱澎生(2001)論述明清時政府法律、工作倫理的限制使商人雇用工人同聚一處生產具有較大風險,可以反映勞動力組織與管理的成本之高。
雇傭勞動力的報酬是企業管理成本的重要內容,企業主是否能以很低的工資獲得廉價勞動力呢?在個體家庭中,勞動的邊際收益遞減,即使遞減至極低的水平,勞動者仍愿意追加勞動,幾乎可以不計成本。但在企業主而言則不同,他必須按勞動時間平均支付報酬,工人多工作一小時,就得支付一小時的工資,企業主不可能以邊際遞減來支付工資。因此企業主不可能低成本地獲得家庭作坊中廉價的近乎無限供給的勞動。另一方面,任何企業主當然希望雇傭熟練工人,熟練工人進入企業,勞動力的價值只能按簡單勞動來支付報酬,因而所獲工資將被大大低估。馬克思指出,在工場手工業中,由于職能的簡化,工人的技能等學習費用比獨立手工業者要低,勞動力的價值就降低了(馬克思1975:388-389)。因此熟練工人被雇傭到工場里,不可能得到期望的或應得的工資,因為企業主只是利用其單一技能,他在其他方面的技能、知識、特長都沒有用武之地了。勞動力的價值被降低,工資必然也不高。因此熟練工匠不如在自己的家庭作坊中,勞動力價值會得到充分的釋放,總體收益通常也會高一些。李伯重(2000:第十章)對江南的考察說明了這一點,江南勞動力素質較高,能夠獨立經營小作坊,而不必依賴更大的組織直接管理生產活動。
可見,作為要素市場的勞動市場發育滯緩,使企業組織通過勞動市場替代商品市場過程中發生的交易費用較高,是否足以抵消規模經營所帶來的收益,留待本文第五部分分析。我們再來看一看企業組織的生產費用。
四、生產工具與設備的制約:生產費用與效益
資本的集中、生產的集中隨著生產設備的復雜程度而加強,個體小手工業者只能適應簡單工具,復雜的、大型的、或昂貴的工具必然促進資本對生產資料控制的深入,對生產過程控制的強化。英國工業革命的發生過程就是充分的證明。無論在西歐還是在中國,重工業、采礦業等更多是由商人直接投資與管理,而輕工業中最常見的則是個體工匠的小作坊。明清中國還可以找到其他實例。在需要大型設備的領域,如蘇州的踹布業,在特殊形態下形成了集體勞動。而棉紡織業中商人資本投資設備出租的“放機”現象,到20世紀有了機制織紗后才出現。生產資料的大型化有助于商人資本直接投入生產,擴大企業組織,但這種現象在明清中國尤為稀見,關鍵的原因就是大型設備與廠房的費用太高。
關于這一點,李伯重(2000)對江南企業組織的考察富有說服力。企業規模的擴大,首先決定于生產設備規模。在英國,以水力為動力的主導生產設備是企業規模擴大的關鍵。江南的水力、畜力資源貧乏,畜力成本很高。如在榨油業中,油碾越大,油坊的規模也越大,經濟效益也越佳,但因飼養牛用作畜力的成本太高,油坊的規模受到限制。其次,勞動場所是擴大企業規模的另一關鍵。江南磚瓦石料、木材緊缺,大型房屋的造價十分昂貴,企業規模擴大受到嚴重阻礙[7]。
再來看技術革命。單純的技術發明不一定能帶來技術革命,它需要特定的外部條件與之配合,需要制度創新為技術創新與推廣鋪路。對于技術革新與設施引進,個體生產者通常是排斥的,因為可能需要額外的支出,或者將危及其生產獨立性(HansMedick,1981)。行會也不歡迎,因為它會改變既有的產業秩序。17世紀絲帶織機在荷蘭遲遲得不到采用,手搖織襪機從英國引入倫巴第也未能成功,它們在英國則得到開發(多梅尼科·塞拉1988)。這些相對于中國一些發明來說要幸運得多。元代出現的偉大發明水轉大紡車至明清銷聲匿跡(李伯重1985)。清初戴梓發明的火器“連珠銃”,一次可填發28發子彈,又造出蟠腸槍和威遠將軍炮,但以“騎射乃滿洲根本”的清王朝,忌憚削弱八旗軍的傳統與優勢,不予采用,還將他發配充軍。這是技術發明受到制度制約而窒息的典型事例。在形成了路徑依賴的行業,某一環節的技術發明,因為它的使用會引起整個產業體系其他環節的相應變化,也就是說必須改變整個產業系統才能使技術發明得到廣泛的應用。英國棉紡業直到17世紀才自印度傳入,毛織業這一傳統工業則歷史悠久得多,但工業革命發生在棉紡織業。保爾·芒圖(1983)分析道,一個沒有傳統的新工業,未被墨守陳規的傳統所束縛,它處在那些阻止或延緩技術進步的法規之外,它好像是一種對發明和各種創舉開放的試驗場地。毛紡織業則太保守了,受到特權的保護,所以不能通過技術革新來自行完成自己的變革。也就是說路徑依賴阻礙了英國毛紡織業技術創新。明清中國的紡織業從生產到市場都已形成成熟的體系,因此如水轉大紡車之類技術革新不僅未能帶動整個產業體系的變化,相反自身要受到這個產業體系的制約。如果說英國毛紡織業受到特權的保護,是否可以說,明清的絲棉紡織業受到市場結構與家庭經營形式的“保護”而阻礙了技術革新呢?對此我們暫且提出假設而不予展開論述,但有一點是肯定的,現代社會看得更清楚,沒有市場需求尤其是廠商需求的刺激,技術創新從發明到推廣應用就會缺乏原生動力。像英國馬修·博爾頓那樣的廠商,敢于負擔瓦特的發明及其應用的費用,在中國找不到其蹤影。
盡管中國技術創新遲滯的原因十分復雜,本文無法深入展開,但這一現象卻是長期存在的,而技術創新的遲滯、生產工具的輕巧簡單,使個體小生產的手工業如魚得水,卻使資本控制生產資料的進程停滯不前,企業組織因小規模的設備、廠房等的限制而未能擴大。看來,當市場已經發展到一定的高度,當商人資本已經滲入生產領域形成散工制等組織形式,卻未能向前推進,控制生產工具,關鍵的原因還是設備、技術沒有足夠改進,使得企業替代市場缺乏強大的推動。
五、分工與專業化的實現:通過市場網絡還是企業組織
分工與專業化通過市場來實現,也可轉而通過組織來安排,在利潤與收益既定的條件下,制度選擇視各自的交易費用而定。分工與專業化的不同實現途徑,與分工的類別與特征相關。斯卡爾培克、馬克思將分工劃為三種:一般分工、特殊分工、個別分工(馬克思1975:389-394)。個別分工就是組織內部的分工,前兩種分工都屬于社會分工。在社會分工中,每個人所生產的只是一種中間產品。使這些獨立勞動發生聯系的,是各自的產品都作為商品而存在[8]。在工場分工中,局部工人不生產商品。社會內部的分工以不同勞動部門的買賣為媒介,工場內各局部勞動之間的聯系,以不同的勞動力出賣給同一個資本家,而這個資本家把它們作為一個結合勞動力來使用為媒介。工場分工以生產資料積聚在一個資本家手中為前提;社會分工則以生產資料分散在許多互不依賴的商品生產者中間為前提。工場分工以資本家對人的絕對權威為前提,人只是資本家所占有的總機構的部分;社會分工則使獨立的商品生產者互相對立,只承認市場競爭的權威。社會內部的分工與工場內部的分工,不僅有程度上的差別而且有本質的不同。
社會分工的實現通過商品市場,組織內分工的實現通過要素市場,在不同的市場體系之下,各自的交易費用不同。傳統中國與中世紀西歐,在市場結構與體系特征上存在一定的差異(龍登高1992a)。中國傳統市場自宋以來形成了等級體系,這是基于個體小生產者市場主體行為特征的市場結構,也與行政等級體系相輔相成。細密的網絡,將分散的細小的個體小生產者卷入市場體系之中,并通過有效的價格傳遞,組織各地的商品集中與分銷。在這種市場體系中的商品,由于小農與小生產者的低生產成本,以及市場體系本身有效地傳遞價格信號、運輸成本的低廉,商品總的成本較低。
與中國相比,西歐中世紀市場網絡沒有那么細密,通過各地每年一個月的市集,各莊園之間,以行會來組織的工商業城市之間,大規模的商品流通引人注目。個體農戶與市場的聯系沒有那么密切,但與市場相關聯的生產組織中的分工卻要發達一些。這種差異似乎可驗證楊小凱的命題[9],西歐沒有形成傳統中國的市場等級體系,可以說是“多中心層系”,商品市場的效率要低一些。英國的道路狀況較差,交通運輸成本較高,通信和運輸費用的昂貴阻礙著交易。安女王時期,英國市場雖然優于法國和德國,但市場體系也不夠完善,分為許多彼此孤立的地區性市場。除倫敦外,沒有一個城市同王國其余各地保持著經常的交易關系;至于鄉村的貿易范圍,很少超過鄰近城市之外[10]。由于商品市場的交易成本較高,而勞動力市場具有一定的潛力,于是商人力圖利用要素市場的優勢,通過企業組織及擴大規模,可望降低或抵消市場交易費用。[11]
在明清中國,我們確乎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市場發達的地區和行業中,分工與專業化更多地通過商品市場來實現,也就是社會分工較發達,甚至一些可以在企業組織內完成的分工也由更具效率的社會分工在市場體系中完成。從資本主義萌芽的研究成果中我們看到,在市場欠發達、勞動分工較少的行業與地區,如遠離商品市場的采礦業、伐木業、池鹽海鹽業、航運業等,以及農產品加工業,出現較多的商人雇主制即商人雇工生產的企業組織。相反,在勞動分工較細致的工業中,往往通過商品市場來建立工業運轉體系,如絲織業與陶瓷業,最為典型的就是江南絲織業中的包買商。
清代江南絲織業已經形成一個復雜的組織體系,賬房把絲織的每一個工序都組織起來,支配著機戶,也支配著染坊、掉經娘、絡緯工、牽經接頭工等,形成一個龐大的工業體系(吳承明1985:379)。這是通過發料收貨這一基本形式實現的,每一個環節都通過商品市場聯系起來,這個組織體系主要依托發達的市場關系。散工制的組織形式,通過長期而穩定的契約關系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交易成本[12],成功地實現了成本外部化和收益內部化。如果要以企業組織來替代這些市場關系,必然要以要素市場替代商品市場,那么其交易費用之大可以想見。
景德鎮和廣東石灣的陶瓷業中的許多工種,都專業化為獨立的行、店,窯戶中的一行只生產一類產品。這種專業化,一方面可提高技術和效率,另一方面也使得生產單位分散細小。吳承明(1985:27)指出,工場手工業的勞動分工,明清時期不能和歐洲工場手工業時期的情形相比。這其中有一種情況是,由于場外分工發達,場內分工反而簡化。陶瓷業因過分專業化,窯、作、行、店林立,互為分工協作關系,其工場手工業的規模反而十分可憐。
馬克思(1975:379-389)還把工場手工業分為兩種基本形式:結合的工場、有機的工場。前者適合的行業是,由多種獨立部件組成,最終產品就是把這些獨立部件裝配起來,如鐘表制作。這些行業中,局部勞動本身可以作為彼此獨立的手工業進行,局部工人在同一工場中的結合是偶然的,只有例外的情形下才有利。因為在家里勞動的工人之間的競爭十分激烈,生產分為性質不同的過程,人們不大可能使用共同的勞動資料;而且在分散生產的情況下,資本家可節省廠房等費用[13]。真正的技術的統一只有在轉化為機器生產時才能產生。
有機的工場,則常常出現于這樣的行業:制品要順序地經過一系列的階段過程,典型的行業如制針、制瓶、玻璃制造等。如果把原來分散的手工業結合起來,就縮短了制品的各個特殊生產階段之間的空間聯系,減少了階段轉移過程中的時間耗費與勞動耗費。不同的階段過程由時間上的順序進行變成了空間上的并存,形成了連續性、劃一性、規則性、秩序性。
盡管實際區分起來頗具困難,但馬克思的分析邏輯上是有道理的,而且他論證了結合的工場所具有的偶然性。不過,在明清中國我們看到的情形是,不僅結合的工場罕見于世,而且本來適合形成有機的工場的行業,仍是散工制主導,或者由商品市場關系主導。制瓷與制針、制瓶、制玻璃很相似,然而沒有形成有機的工場,反而分成專業化很強的各種工序與行店。紡織業多少也應屬于這一類時序連續性的行業,而與部件匯總的鐘表業區別更大,也沒有形成有機的工場。這進一步論證了我們的觀點,與西歐相比,傳統中國的分工與專業化更多地通過市場來實現,要素市場替代商品市場的企業組織的發展滯緩。正如楊小凱(1999:411-412)的數理分析所示,最終產品生產和中間產品生產的分工,以及交換某種中間產品的交易效率低于受雇生產該中間產品的勞動交易,是企業產生的必要且充分的條件。這一條件在傳統中國尚未出現。
由于商品市場的發達,與前述勞動力市場的滯后,從市場購買中間產品與制成品,較之于購買生產要素,能夠更充分地利用和實現分工與專業化及其具有的優勢。
六、余論
以上所論,在清代蘇州等地的踹布作坊形態中得到充分的體現。踹坊需要使用大型的工具設備,因而形成了二三十人規模的集體勞動。但這種企業組織比較特殊。踹坊由包頭投資固定資產開設,踹匠由包頭管理,但踹匠工資即可變資本,由商人(布號)計件支付,包頭每人每月抽取三錢六分。[14]包頭相當于布號,但同時踹坊具有一定的獨立性,二者之間有矛盾,時有訴訟。為什么布號商人不直接投資于踹坊生產?主要是為了減少組織管理工人生產的成本,因為踹匠都是外來游民,兇悍之輩,并且抱成一團,很難約束,即使本地的豪強包頭也不易駕馭,外來的商人將付出更大的管理成本。為什么包頭踹坊不完全獨立地經營,建立縱向一體化的組織呢?如果踹坊主自己收購布匹,加工后自己發售,那么其經營成本將很高,而且難以抵御市場風險,而布商已經建立營銷網絡。因此,在這里,布商、踹坊主、踹匠三者之間,主要通過市場關系建立了這種獨特的棉布加工與銷售體系,布商與踹坊主之間的委托關系實際上通過商品買賣來維系,布商與踹匠之間的雇傭關系也因包頭的中介而轉變成通過市場的某種委托關系,踹坊主與踹匠之間只存在組織與管理關系,雇傭色彩較弱。通過這種復雜的關系,尤其是通過發達的市場,替代了勞動組織。勞動組織的高成本,由商人與作坊主分擔。這種產業經營組織體系,形成并建基于長期而穩定的契約關系之上,長期而穩定的契約關系能有效地降低交易成本(德姆塞茨1999),也表明這種組織體系的成熟性與合理性。
本文所論,在明清企業組織的趨勢性發展中得到了映證。絲織業在明后期已出現工場手工業的雛型,到市場更成熟的清中葉反而基本消失;它被較完備的包買商形式所代替了(吳承明1985:26)。在最發達的江南,工業企業形式一直以獨立經營的小手工操作的作坊為主,它是江南企業發展的最佳組織形式,規模較大的作坊或手工工場,不僅數量不多,而且還有減少的趨勢(李伯重2000,第十章)。這種趨勢還延續到近代,一些實例也可資佐證。19世紀中后期杭州的蔣廷桂,由于經營有方,綢機增至10臺,雇了學徒幫工。但他不再增添機只,而是充當包買商向小機戶放料收貨,到光緒初年,他的蔣廣昌綢莊支配的織機已達300臺。后來他從日本購置鐵制綢機,建立織綢工廠。同時仍充當包買商(胡慎康,1985)。這個故事耐人尋味。蔣氏作坊的規模達到10臺織機后,并沒有繼續擴大規模后,而是充當包買商,這顯然是包買商能帶來更多的利潤,高于機戶規模經濟的效益。作坊規模經濟的效益直到先進機器的引入才得到發揮,即便此時,企業組織的利潤也還不足以排斥包買商體系下的個體機戶經營。
農業企業的特征與工業企業組織類似,命運也相似,與工業、農業組織形成對照,商業企業組織的發展則引人注目,尤其如一些晉商、徽商建立了全國范圍的龐大組織網絡(張正明1995;張海鵬1995),在許多行業中,商業企業將各種手工作坊聯結而成有機的體系。這是因為市場體系與分工特征適合商業企業組織的發展。例如,對它影響最大的是商品市場而不是勞動市場;產品質量考核只需把握成品環節而無需進入生產過程;社會內分工與分散化生產給它提供了更多的商業機會與更大的舞臺;它對大型廠房與設備的要求較少,倉儲或庫房可以通過加快流通速度來緩解;而規模經濟的效益,它可以通過擴大營銷數量在龐大的市場中充分實現。
如果說企業組織的發展存在各種制度,那么,個體手工業獨立經營則在市場體系中如魚得水,富有生命力。家庭企業中,勞動不存在考核費用,要素市場的滯后不會對它產生影響;輕巧簡單的設備,個體家庭得心應手,并以熟練的技術、不計成本的勞動耗費增強效率;細密的市場網絡,使家庭工業能夠依托社會分工與專業化而獲益,并彌補家庭內分工與專業化的缺陷。凡此都與科層企業組織的命運形成對照。種種跡象表明,與擴大的企業組織形式相比,個體家庭經營在中國傳統市場體系中具有很強的生命力與制度合理性。紡織業等主要行業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形成了路徑依賴與歷史慣性,如果缺乏必要的刺激,這種局面很難改變,傳統時代的這種突破尤其如此。
散工制所反映的產業經營組織形式,不是棉布、絲織業獨有的現象,其他行業與部門中也不乏其例;它以江南為典型,其他區域也廣泛存在;它以明清時期為突出,但溯其源可直追宋元,順其流在近代仍具有強烈的趨勢性表現。因此,它不是偶然的現象,而具有普遍性意義,并足以反映傳統中國產業經營組織形式的本質特征,本文從傳統經濟與社會結構的分析也是為了強化這一論點。
參考文獻
阿爾奇安與德姆塞茨(AlchianandDemsetz),1999,《生產、信息成本與經濟組織》,載德姆塞茨《所有權、控制與企業》,經濟科學出版社中譯本。
保爾·芒圖,1983,《十八世紀產業革命》,商務印書館中譯本。
多梅尼科·塞拉,1988,《1500-1700歐洲的工業》,載卡洛·M·奇波拉主編《歐洲經濟史》第二卷,商務印書館中譯本。
德姆塞茨,1999,《企業理論再認識》,載《所有權、控制與企業》,經濟科學出版社中譯本。
范金民、金文,1995,《江南絲綢史》,農業出版社
HansMedick,1981,inKriedte,Peter,HansMedick&JurgenSchlumbohm.IndustrializationbeforeIndustrialization,CambridgeUniversity.
胡慎康,1985,杭州蔣廣昌綢莊發家史紀要,油印本。轉引自吳承明(1985:382)。
JohnHicks:1969,ATheoryofEconomicHistory,Oxford.中譯本《經濟史理論》,商務印書館,1987
科斯,1994,企業的性質,載《論生產的制度結構》,上海三聯書店中譯本。
李伯重,1985,水轉大紡車及其歷史命運,載《平準學刊》第三輯上冊,中國商業出版社。
2000,《江南早期工業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龍登高,1992a,封建市場比較研究:宋代中國與西歐中古盛期,載《紀念李埏教授從事學術活動五十周年史學論文集》,云南大學出版社。
1992b,《個體小農家庭經營方式的歷史演進》,《云南民族學院學報》第四期。
1996,個體小與傳統市場,《中國經濟史研究》第2期。
1997,《中國傳統市場發展史》人民出版社。
羅友枝(E.S.Rawski),1990,CompetitiveMarketsasanObstaclstoEconomicDevelopment,China’sMarketEconomyinTransition,EditedbyYung-sanLeeandTs’ui-jungLiu,AcademicSinica.
MarkBlaug,1985,EconomicTheoryinRetrospect,CambridgeUniversityPpress。
諾思,1994,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上海三聯書店中譯本。
錢德勒,1987,看得見的手,商務印書館中譯本。
邱澎生,2001,《商人如何改造生產組織?清代前期蘇州棉絲工業的放料制生產》,江南城市工業與大眾文化研討會論文。
全漢升,1996,清代蘇州的踹布業,中國近代經濟史論叢,稻禾出版社。
吳承明,1985,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的成果集中于許滌新、吳承明主編《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97,《市場·近代化·經濟史論》,云南大學出版社。
徐新吾,1992,《江南土布史》,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楊小凱黃有光,1999,專業化與經濟組織,經濟科學出版社中譯本。
伊懋可(MarkElvin),1973,ThePatternoftheChinesepast,StanfordUniversityPress.
張海鵬等主編,1995,《徽商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