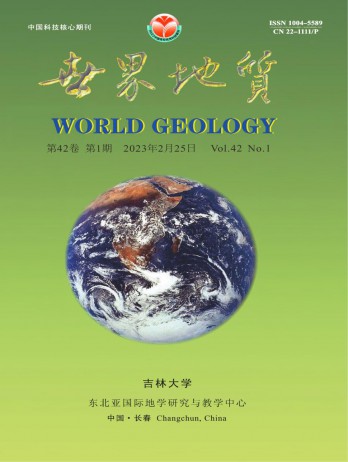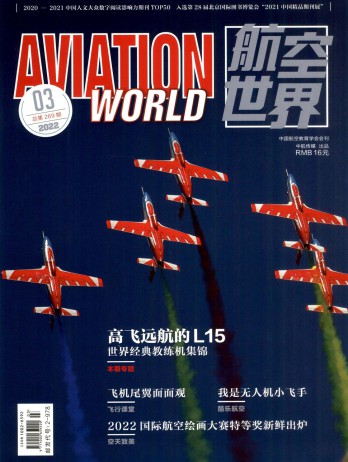本科機械論文精品(七篇)
時間:2023-02-27 11:21:33
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本科機械論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學者王元化也被推重為“時代的思者”①。雖然作為學者或思想者,王元化都難以完全納入“比較文學”論域,后者卻可能是感觸前者獨特風貌的一個有效視角,而前者也可能為后者提示“中國氣派”的啟示。就王元化學術方面而言,一位前輩文藝學者將之梳理概括為八個方面后寫道:“20世紀上半葉,中國出了不少學術大師,如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魯迅、、郭沫若等”。而及至21世紀,“王元化作為一代學術大師的意義和價值,似乎還不曾被更多的人所認識和揭示”②。在改革開放以后形成的“比較文學”學科領域中,著名法國文學研究者錢林森《緬懷遠去的智者———王元化先生與〈跨文化對話〉二三事》中寫道:“國際雙語論叢《跨文化對話》自1998年創刊至今,已邁過10年歷程了。……不久前離世的王元化先生,他為《跨文化對話》留下的思考和文字,更值得我們珍惜、懷念”③。王元化被推重為“比較文學”研究領域開拓者的代表作是1979年出版的《文心雕龍創作論》。該書在全國首屆(1979~1989)比較文學圖書評獎活動中獲“榮譽獎”④。學者趙毅衡當年評論:“一九七九年或許是我國比較文學研究進入‘自覺期’的一年:錢鐘書《舊文四篇》、《管錐篇》前四卷、楊絳《春泥集》、范存忠《英國文學語言論文集》、王元化《文心雕龍創作論》,這些解放后出版物中中西比較文學內容最集中的書籍,都出現于一九七九年。”①季羨林先生在更早的1981年寫道:“應該把中國文藝理論同歐洲的文藝理論比較一下,進行深入的探討,一定能把中國文藝理論的許多術語用明確的科學語言表達出來。
做到這一點真是功德無量。你在這方面著了先鞭。”②王元化另一部代表作《思辨隨筆》于1995年獲第二屆中國國家圖書獎。著名翻譯家蕭乾先生在《〈思辨隨筆〉不可不讀》中寫道:“這里論述的真是從中至外,從古至今:從孔子、劉勰到魯迅、,從莎士比亞到普希金,沒有冗長引句,更不見老生常談,全是作者的思緒和心得。他對莎劇有些評論如譯出來傳到國外,估計必會贏得西方莎學家們的贊賞,因為其中飽含著東方人的智慧卓見。”③如果說蕭乾評語中對“東方人智慧”的強調在中國比較文學研究界是先著一鞭,那么其所思所見與王元化本人同時期關于中西文化比較的主導思想之強調是不謀而合:研究中國文化,不可避免地需要以西學作為比較的參照系,但又不可以西學為主體,用中國文化去比附。恕我再一次借用正在受人指摘的余英時的直率說法:“今天的文化危機特別表現在知識分子的浮躁心理上,仰慕西方而不知西方文化的底蘊,憎恨傳統文化又不知傳統文化為何物。”④并非偶然的是,十年后日本學者將《思辨隨筆》作為《王元化著作集》之一而完整譯介⑤。《思辨隨筆》于2004年增補修訂為《思辨錄》⑥。有的高校教師開始將之作為“大學本科生和研究生入學時必讀的教科書”⑦。最近一位承擔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的年輕學者在《王元化〈思辨錄〉的方法論意義》專題論文中提出:“《思辨錄》體大思精慮全、圓融中外古今,對其展開全面研究是一門大學問。”⑧筆者初步考察統計,《思辨錄》全書出現的外國作家與文學人物姓名不下三百之數。如果以外國文學作為“比較文學”參照系,則該書內涵之豐富也可見一斑。
王元化學術中的“比較文學”因素還可追溯到其歷年乃至早期著述中。例如文藝評論集《向著真實》初版于1952年,其中所及的外國文學家不僅有契訶夫、車爾尼雪夫斯基、別林斯基、羅曼?羅蘭、果戈理、卓別林,還包括法國作家左拉、美國作家考德威爾、捷克作家伏契克,以及委內瑞拉詩人等。該書再版后記回顧道:“我寫下了對自己所喜愛的某些作家的一些感受。其中有些看法現在雖然已有所變化,但對于這些引導我認識生活和怎樣對待文學事業的先驅,我始終懷著青年時代的崇敬心情。今天重讀這些文字,我的心中仍激起當年的感情波瀾。”⑨一位年長學者回憶八十年代末讀到《向著真實》與《文心雕龍創作論》二書時的心情:“那時,我在一些前輩鼓勵下,正起步于比較文學教學與研究,并開始招收比較文學方向的研究生。相遇王先生這兩部著作,對我而言,真是不期而遇的‘機緣’。《向著真實》這部處處充滿真知灼見的評論文集中,最引起我注意和興趣、且對我產生影響的,是他評論羅曼?羅蘭《約翰?克利斯朵夫》的兩篇文章,先生對羅蘭作品認識獨到,見解高遠,我不僅在自己的論作中加以征引,也在對研究生授課中多次介紹過。”①王元化青年時代最初論文是1939年發表的《魯迅與尼采》。他晚年自述該文“受到了由日文轉譯過來的蘇聯文藝理論影響”,其中有“機械論的痕跡”②。然而在中國現代文學思想史敘事中,迄今它依然不失為“三十年代關于魯迅的最有分量的論文之一”③。《魯迅與尼采》的標題與今天“比較文學”研究的通常模式相契。該文作為王元化最初發表而產生影響的論文,意味著其學術生涯中的某種潛在基質。如果說這種基質與后來引進的“比較文學”研究視閾和方法不謀而合,那么王元化自1939年迄至去世的2008年,在近七十年中先后出版的四十余種著述中,都可能包含“中國比較文學”研究的獨特因素和資源。
二、“比較文學方法”與“綜合研究法”
原初意義上的“比較文學”基于兩個要素:一為文學對象,二為外文研譯。前者是比較文學的特定對象,后者是賴以成立的前提。就此而言,王元化學術至少包含若干原初意義的“比較文學”因素。例如他的莎士比亞研究包括對西方莎劇論文的譯介。他的《文心雕龍》研究,前期成果之一是對西方“文學風格”代表性論文的譯介,后者成書為《文學風格論》④。此外,王元化還與父親王維周教授合譯過《革命親歷記》⑤。然而在中國語境中,比較文學研究通常也以中譯本為對象。即便在這一場合,研究者是否自覺意識到外文原文與中文譯文之間可能存在意味差異乃至歧義,這無疑會影響到他所作判斷和所下結論是否中肯合理。這種差異乃至歧義尤其表現在一些專門術語上。因此,至少就中外文藝理論的比較研究而言,對中外術語意味之差異的清醒認識,以及基于這種認識的追溯考辨斟酌等,理應是研究者的必要條件和基本素質。王元化學術中的“比較文學”因素也蘊含于他對漢譯西方著作的研讀和闡釋中。這方面他所提供的啟示之一是,對于西方著作中的一些關鍵性理論術語,必須結合外文語源和語境而盡可能充分辨析、追溯和考量。例如他的《讀黑格爾》中多處研討了黑格爾術語的中譯問題。諸如:“情志”、“情致”、“”三者相對于黑格爾原著中古希臘詞“”何者更為恰當;“知性”較之于舊譯“悟性”或“理解力”為什么更能妥切傳達德文原著“Verstand”之旨;“總念”、“概念”之于德文“Begriff”的孰所優劣;中國古典美學“氣韻生動”、“生氣灌注”與黑格爾美學“beseelt”的漢譯關系;被英譯為“sense”(感覺)的德文“sinn”是否可以譯為“藝術敏感”;為什么應該用“寧靜”來替代中文舊譯的“靜穆”,等等⑥。這里我們以《讀黑格爾》用“情志”翻譯“”的一例觀之。
后者在黑格爾德文原著中就是一個源于古希臘的外來詞,并且黑格爾本人認為它在德文中很難找到確切譯詞。而據《讀黑格爾》對“”詞的考察:它在英文中譯作“Pathos”(意為悲哀,哀愁,動情力,悲愴性等),在拉丁語中譯作“Qual”(意指本原的痛苦),在恩格斯著作中被解釋為“苦悶”,在中文舊譯中轉成“情致綿綿”。這些譯詞相互歧異,究竟如何漢譯為恰?王元化考辨的結論是:“”這個詞不僅涉及情感方面,也潛在“志”的意蘊,它指謂的是一種“合理的情緒方面的力量”;中文舊譯“情致綿綿”未能傳達該詞的“志”意,英譯“Pathos”(悲愴情感)也遺漏了該詞的倫理意味①。這個例子至少表明,王元化對黑格爾術語的把握是經過多方考究和反復斟酌的。一方面,其結合黑格爾理論體系背景而辨析的方法是超出了一般語言翻譯家的關注所及;另一方面,其對該詞語源的盡可能追根溯源,亦足為重思想而輕學術的年輕后輩有所借鑒。就外來的“比較文學”方法而言,通常認為主要有“平行研究”與“影響研究”兩種。而這兩種方法在王元化著述中多處可見。這里僅就平行研究方面管窺一斑:在我讀過的劇作中,我把具有這種特點的劇本稱作是“散文性戲劇”,將它與“傳奇性戲劇”相區別。……我對散文性戲劇和傳奇性戲劇所作的比較說明,在我過去所寫的文字中曾留下了痕跡。②王元化以“散文性戲劇”與“傳奇性戲劇”來概括契訶夫與莎士比亞作品的不同特點,這顯然可納入“平行比較”。據考察,我國建國初戲劇界關于戲劇結構的分類,有開放式、閉鎖式、人物展覽式的三類型說;至上世紀80年代有純戲劇式、史詩式、散文式、詩式、電影式的五類型說,其中將莎士比亞戲劇作為史詩式結構的典型,契訶夫戲劇作為散文式結構的典型;同期又有論者以“非戲劇化傾向”來指謂契訶夫戲劇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