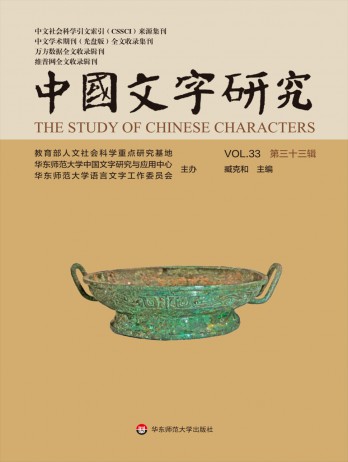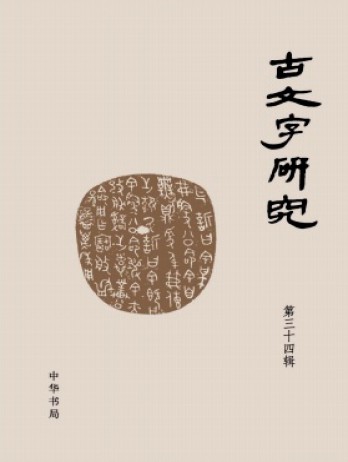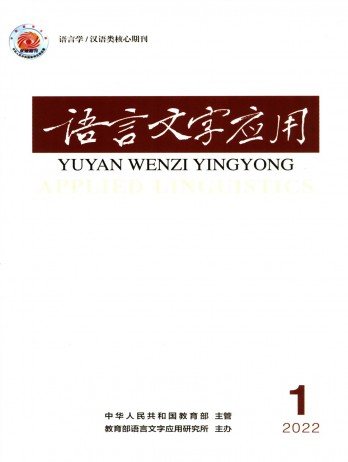文字藝術論文精品(七篇)
時間:2022-04-22 04:42:17
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nèi)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文字藝術論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chuàng)作。

篇(1)
中國書法藝術融合運用于視覺傳達設計的重要性及必然性
按照馬斯洛的需求層次學說,人的需要存在先后和高低順序。隨著現(xiàn)代科技的發(fā)展和社會生產(chǎn)力的提高,人類已經(jīng)逐步滿足了自己對物質(zhì)的需求,那么對更高層次的精深需求也就成為追求的目標。所以,現(xiàn)代視覺傳達設計不能僅停留在介紹產(chǎn)品的功用和質(zhì)量方面信息的快捷獲取,更多的應該是給受眾帶來精神愉悅和審美認同。要獲得這樣的審美享受和情感上的滿足,就需要不斷的增加設計作品的文化內(nèi)涵。畢竟,任何民族對自己的傳統(tǒng)文化都有特定的感情,其設計活動以民族的傳統(tǒng)文化精神融入其中,定能引起受眾的共鳴。
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博大精深,蘊涵著豐厚的思想內(nèi)涵,書法在其生成與發(fā)展過程中,與整個中國傳統(tǒng)文化形成了密不可分的關系。首先,書法藝術是以漢字為載體的,而漢字是表意兼表形的文字,相對于其他文字來說,其可塑性較強。同時,因漢字本身是中華名族的偉大創(chuàng)造,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重要載體,所以,中國書法在其生成之時便沉淀著歷史文化的印記。其次,中國傳統(tǒng)的文學藝術給書法家以啟迪與滋養(yǎng),使得大量的藝術形象能在無形中融入書法藝術的創(chuàng)作過程。再次,中國傳統(tǒng)哲學思想和美學思想帶給書法藝術的是空前巨大的影響。它對書法思想、書法精神、書法審美以及書法創(chuàng)作都產(chǎn)生著深刻的影響。“沒有特定的民族文化、民族哲學、美學精神,便沒有特有的中國書法精神;沒有對民族傳統(tǒng)文化、民族傳統(tǒng)哲學、美學的理解,對書法精神的理解也將是不可能的。”
由此可見,書法藝術與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的文學、哲學以及美學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成為燦爛的中華文化中獨樹一幟的特色藝術。筆者認為,設計也是一種文化創(chuàng)造,其目的也是要傳播中國文化,而中國書法恰好能將民族文化精神給予合理的詮釋。因此,書法藝術理應成為現(xiàn)代視覺傳達設計中的至關重要的元素。
書法是我國特有的藝術形式,在視覺傳達設計中運用書法字體,與圖形相結合,彼此交相輝映,為視覺傳達設計平添一種藝術的靈氣與文化的意蘊,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如圖3)。在信息化高速發(fā)展的時代,青少年對書法的把握與書寫顯然沒有網(wǎng)絡那般有吸引力,這顯然是應當引起重視的問題,因此,將書法與視覺傳達設計相結合,在一定意義上拓展了書法藝術的存在空間。同時,若在青少年的日常生活中接觸的網(wǎng)絡、商品包裝、書籍等到處都能見到體現(xiàn)中國文化精神的書法,則為不懂得書法藝術欣賞的青少年提供書法欣賞的環(huán)境,使其能從設計作品中或多或少的感受到書法藝術的博大精深,進而漸漸領略書法藝術的真諦而喜歡上書法。當然,設計者在將書法藝術與平面設計相結合時,需打破常規(guī),在繼承傳統(tǒng)的同時利用計算機等現(xiàn)代科技進行調(diào)整布局、變換色彩等設計,達到良好的視覺傳達效果。
書法藝術在視覺傳達設計中的創(chuàng)新運用
近幾年來的視覺傳達設計中,對于書法藝術的運用日漸增多,這也暗示著書法在視覺傳達設計領域的廣泛前景。現(xiàn)代視覺傳達設計無論是包裝、裝飾、標志、書籍、招貼、展示、廣告、影視節(jié)目、動畫以及舞臺背景等設計中,都有借鑒書法藝術的表現(xiàn)形式,大大拓寬了現(xiàn)代視覺傳達設計的領域。
那么如何在視覺傳達設計中創(chuàng)新運用書法藝術?首先,設計從業(yè)人員的設計觀念要與時俱進,自覺學習中國傳統(tǒng)文化藝術,尤其是書法的學習。只有當設計者領悟了書法藝術,運用起來才會得心應手,將書法藝術的富有個性和充滿生命活力的線條與視覺傳達設計結合,從而傳遞出豐富的文化內(nèi)涵。
其次,設計者對不同書體的書寫特征要有清楚認識,通過對設計對象的特征。如隸書,筆劃蠶頭燕尾,通過筆墨的肥瘦方圓,或伸,或屈,使文字具有雄闊嚴整而又舒展靈動的氣度;行書則行飛自如,瀟灑飄逸,筆未落,意先存,氣勢蘊蓄。
因此,在視覺傳達設計中,設計者要對書法藝術進行深加工處理,找尋更貼切的符合受眾視覺審美習慣的表現(xiàn)形式來傳達設計作品的信息,增強作品的感染力。以下是兩種具體的書法在視覺傳達設計中的表現(xiàn)形式。
1.替構
這里說的替構,是指將書法字形分解開,并將其中的一部分用其他物象代替,借以構成新的形象,并賦予這種經(jīng)替換后的整體形態(tài)以新的含義。如圖4,是余秉楠先生設計的招貼《家》,將“家”字最后一捺借寶島臺灣的地形輪廓替代,寓意中國海峽兩岸是一家,是統(tǒng)一不可分割的整體,傳達出極強的民族情感,深化了主題思想。
2.符號化結構設計
中國的漢字的獨特之處在于,它是一種象形文字,在形體上逐漸由圖形變?yōu)橛晒P畫構成的方塊形符號,有其獨特的造型之美。那若將以漢字為載體的書法藝術中的抽象元素(如各種筆畫)通過簡化來創(chuàng)新運用,設計作品則呈現(xiàn)出與眾不同的東方文化韻味。比如在書體的運用上,篆書具有古代象形文字的古樸感,其圖形的抽象趣味在近代的圖案表現(xiàn)上已經(jīng)被藝術化。在當代設計中,尤其是國內(nèi)視覺傳達設計中,多把篆書應用于賀年卡、請?zhí)⒒照聢D案等設計。例如2008年北京奧運會的會徽以及2010年上海世博會的會徽將書法藝術巧妙的運用到標志設計中。
2008年北京奧運會“舞動的北京”是本屆奧運會的中心形象。這是有篆刻的印章構成圖案(如圖5)。篆刻是中國最古老也最具特色的藝術形式之一,篆書的書法體現(xiàn)了中國藝術“書畫同源”的特征。北京的“京”字在印章紅色背景中幻化為舞動的人形,成為“北京歡迎你”的形象寫照,它體現(xiàn)了中國人民對于世界人民的熱情友好的態(tài)度。北京奧運會“篆書之美”的體育圖形標志也是以篆字筆畫為基本形式,融合了古代甲骨文、金文等文字的形象意趣,也達到了現(xiàn)代圖形設計“簡化”和“一致性”的要求,從而易于識別、記憶和使用,同時它又與中國印的會徽保持了一致性(如圖6)。這些圖標設計都彰顯了中國文化的深厚底蘊和強烈的民族文化特色。
篇(2)
關鍵詞:比喻,《壇經(jīng)》,英譯
1.引言
作為禪宗六代祖師慧能言語記錄的《六祖壇經(jīng)》,是唯一一部以“經(jīng)”字冠名的中國佛教理論典籍,主要記述了六祖慧能(638-713)的生平事跡和語錄。其文字簡明易讀,近于直白。正如馮友蘭先生在《論禪宗》一文中所說:“禪宗的語錄的特點是,它不用翻譯佛經(jīng)典所用的那種翻譯文體,也不用魏晉隋唐那種駢體文言。它能夠用當時通俗易懂的白話,把佛教和佛學的中心思想簡明扼要地表達出來。”(馮友蘭 1988:6)
但我們在研究中發(fā)現(xiàn),歷代《壇經(jīng)》中都存在大量的修辭手段,主要有反問、設問、比喻、對偶、映襯、比擬等等,如成書于733年的敦煌原本《壇經(jīng)》中就主要運用了省略、引用和比喻的修辭手段(張子開 2003:55),而成書較晚的德異本和宗寶本中修辭手段更多,其中尤以比喻的使用最為頻繁。為什么會出現(xiàn)這種現(xiàn)象呢?在將其譯為英語的過程中,譯者又是如何處理這些比喻的呢?為了便于分析,現(xiàn)將本文所采用的漢英版本交代如下。本文所用漢語版本是96年湖南出版社出版的版本中的漢語本(下文中再提到《壇經(jīng)》漢譯本,即指這個版本),而英譯本亦以這本書中的英譯本為主文學藝術論文,同時參照我國譯者黃茂林(Wong Mau-lam)1930年的譯本和英國學者Christmas Humphreys1953年的修改本。
2.《壇經(jīng)》中比喻修辭手法使用統(tǒng)計
《壇經(jīng)》共十品,各品摘要講的是頓悟與漸悟的差別和方法,說明佛法本無二分,所謂頓漸只是因人的不同而不同;第九宣召品講到當時的則天女皇對慧能宣召及大臣薛簡對大師禪宗大法的領悟和宣揚;最后第十囑咐品是大師臨終前對眾弟子的開悟和囑咐,涉及到三科、三十六對、眾生皆有佛性等思想。下表是對《壇經(jīng)》各品字數(shù)及所使用的比喻手法的統(tǒng)計。
(表一)
品名/比喻手法
字數(shù)
明喻
暗喻
借喻
共計
行由第一
3756
4
1
5
般若第二
2801
9
1
10
疑問第三
1515
1
2
3
定慧第四
1051
3
3
坐禪第五
390
懺悔第六
2412
2
2
4
機緣第七
5087
1
1
2
頓漸第八
2323
1
1
宣召第九
786
1
1
囑咐第十
3557
1
2
3
共計
23718
23
7
篇(3)
關鍵詞:敦煌莫高窟第464窟;回鶻;十地菩薩;北涼;西夏;元代
中圖分類號:K879.2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4106(2012)06-0001-18
第464窟(張大千編號308窟,伯希和編號181窟)位處莫高窟最北端,左與第465窟,右與第463窟相毗鄰,其規(guī)模在莫高窟屬于中等,有前后二室。前室平頂,略有尖脊,頂部地仗大部分脫落,僅存東南角的千佛十余身。南北壁中部繪屏風式方格連環(huán)畫善財五十三參變,畫面受人為損毀嚴重,多處被切割、刻劃。通往后室的西壁甬道口南北二角元代加砌坯墻,向東延長甬道,于西北角和西南角各封堵成獨立的兩個小方室。其中,西北角尚存半截坯墻,而西南角已蕩然無存,唯地面尚存墻跡。后室繪觀音三十二應化現(xiàn)變。
該窟形制較為反常,前室大,而作為主室的后室反而小(圖1),有違常制。何以會出現(xiàn)這種情況呢?學界存在著兩種推論,其一,“推測可能非一次性完工,后來鑿設后室時限于條件而未能挖掘成大于前室的后室”。其二,“從目前窟前崖面現(xiàn)狀看,現(xiàn)在的前室門外鑿崖為北、西、南三堵陡立的平面壁,西頂呈披形,表明原為一個窟室,可能是前室,后隨崖體一起坍毀,或許原來是半石崖半木建組構的前室或窟崖,今毀失。今之前室則為原來的主室”[1]。后一種推測得到了考古學成果的支持[2]。原前室塌毀之遺跡至今依稀可辨。
一 張大千的記述及存在的問題
20世紀40年代初,張大千先生曾對莫高窟北區(qū)包括第464窟在內(nèi)的洞窟進行過挖掘,認為第464窟為“西夏、回鶻修”,對窟中內(nèi)容作了如下敘述:
回鶻佛經(jīng)故事
北壁,二十方,每方間以回鶻文字,高六尺,深一尺六寸半。
南壁,十九方,每方間以回鶻文字。
南壁,佛經(jīng)故事,東端上書“唵嘛彌把密吽”印度等四種文字。
北壁,佛經(jīng)故事,東端上橫書印度等三種文字,下書:“語行無常,是法生滅”①、“唵嘛尼把密吽”。
又回鶻文字:“生滅滅己,寂滅為樂。”
西夏人畫菩薩,一區(qū)。外畫一圓形。西壁正中、上。
觀音、普門品二十方,每方高二尺,廣二尺一寸。西、南、北三壁
佛,四區(qū),龕頂、四面。
又,一區(qū),龕內(nèi)、藻井。
回鶻人畫菩薩,二區(qū)。高三尺四寸,龕門、兩旁。
又上有佛各二區(qū),外畫一圓形,并有回鶻題字。
賢劫千佛,龕門、頂。
回鶻文,兩方,高四尺三寸,廣一尺五寸。剝落,龕內(nèi)東壁、左右
印度文“唵嘛尼把密吽”,四寸大。龕內(nèi)東壁上、間以花枝。[3]
張氏所言第464窟為“西夏、回鶻修”的問題比較復雜,將于下文詳述,這里僅就張氏對窟內(nèi)壁面題字記錄方面所存在的問題略作申述。
其一,前室南壁“東端上書‘唵嘛彌把密吽’印度等四種文字”,由上至下,依次應為用梵文、藏文、回鶻文和漢文書寫的六字真言(圖2)。
其二,前室北壁“東端上橫書印度等三種文字,下書:‘語行無常,是法生滅’、‘唵嘛尼把密吽’。又回鶻文字:‘生滅滅己,寂滅為樂’”(圖3)。所謂“三種文字”,由上至下,依次為梵文、回鶻文和藏文。其下文字,張氏所述有誤,應改為:
其下中間為漢文與八思巴文合璧書寫“唵嘛尼把密吽”右書漢文“語行無常,是法生滅”,左書漢文“生滅滅己,寂滅為樂”。
八思巴文創(chuàng)制于忽必烈時期。忽必烈尊崇藏傳佛教,以藏傳佛教薩迦派第五代祖師八思巴為“國師”,命他以藏文字母為基礎創(chuàng)制新的蒙古文字,以取代原來流行的回鶻式蒙古文,故稱“蒙古新字”,又稱“蒙古國字”,俗稱“八思巴文”。至正六年(1269)二月,這種新文字正式頒行全國。八思巴文是一種拼音文字,絕大多數(shù)字母仿照藏文體式而呈方形,少數(shù)字母采自天城體梵文,還有個別新造字母。這種文字雖作為蒙古國字頒行全國,但未能真正推廣下去。除去政治和文化傳統(tǒng)因素外,主要是因為這種文字字形難以辨識,而且不如回鶻式字母更適用于蒙古語的語言特點,因為蒙古語畢竟和回鶻語一樣,同屬阿爾泰語系,均為黏連語。質(zhì)言之,八思巴文的創(chuàng)制既不適應社會的需要,也有違民族語文發(fā)展的自然規(guī)律,因此,盡管八思巴文名為官方文字,但民間依然使用漢字及回鶻式蒙古文,故其流行不到一個世紀,便隨著元朝的滅亡而銷聲匿跡了[4]。
另外,梵文六字真言的順序應為O mani padme hūm,但在第464窟前室北壁中似乎有書寫混亂之嫌,如尾字hūm(吽)被單寫于第1行,另行開首寫倒數(shù)第五字dme(彌),然后再寫O mani pa(唵嘛尼把)。何以如此?不得而知。
二 西夏石窟說駁議
關于第464窟的時代,學術界主要存在著兩種不同的意見。早在20世紀40年代初,張大千先生即言該窟為“西夏、回鶻修”[3]628-629,已如前述。至于何以如是斷代、定性,不得而知,大概是因為后室西壁有所謂的“西夏人畫菩薩……觀音、普門品……佛”。此后,學界多認為該窟為西夏窟,如敦煌研究院編《敦煌莫高窟內(nèi)容總錄》謂“西夏窟(元重修)”①。是后,學術界多接受西夏說②。近期,西夏藝術史專家謝繼勝再撰文考證,認為第464窟為西夏窟,并以之為據(jù),證明風格與之相近的第465窟亦為西夏窟[5]。
另一種意見則反對西夏說,如西夏石窟考古專家劉玉權在前期調(diào)查和研究的基礎上于1982年完成了對西夏洞窟的分期,從敦煌石窟中分出屬于西夏時期的洞窟88個,其中莫高窟有77個,榆林窟11個,但第464窟未被列入其中[6]。后來,劉先生對原先的分期再作修訂,將西夏洞窟分為二期,其中前期65個窟,后期12個窟,仍未包括第464窟[7]。對劉先生分期持有異議的關友惠先生,同樣也將第464窟排除在西夏窟之外[8]。梁尉英先言其為“元代早期的洞窟”[9],后又改稱“西夏洞窟”[1]。王惠民言西夏說“尚待進一步確定”[10]。
總之,學界對第464窟的分期存在西夏窟和元窟兩種說法,而以西夏說占主流。那么,西夏說之依據(jù)何在?卻一直是個謎,因為從洞窟現(xiàn)存壁畫中除了所謂的具有“西夏特點”的上師蓮花帽之外,看不出西夏石窟的任何特征。謝繼勝先生以認真負責的態(tài)度,考察既有的研究成果,并特意向敦煌研究院有關人員咨詢,得到了如下結果:
通讀梁[尉英]先生的論文,作者并沒有明確說明第464窟定為西夏窟的依據(jù)是什么。主室的壁畫究竟是西夏壁畫還是元代壁畫?筆者在蘭州訪問梁先生時,先生亦語焉不詳。筆者請教敦煌研究院負責清理北區(qū)石窟的彭金章先生,他說第464窟壁畫是否為西夏壁畫他不能斷定,但第464窟的建窟時間比畫面題記顯示得更早,有可能建于北魏。此外,筆者還就第464窟壁畫請教西夏壁畫研究專家劉玉權先生,劉先生稱早期確認此窟是西夏窟,但哪一部分壁畫是西夏壁畫仍不清楚,現(xiàn)在的壁畫可能是元代壁畫。[5]70
可見,言第464窟底層壁畫為西夏者眾,但拿出真憑實據(jù)者鮮。有鑒于此,謝氏著專文對該窟進行研究,確認該窟為西夏壁窟。遺憾的是,同樣未舉出任何有力的證據(jù)。其主要證據(jù)有四,其一為前室南北壁所見兩則來自“大宋”的游人題記。
前室北壁西段題記,刻劃,文曰:“大宋閬州閬中縣錦屏見在西涼府賀家寺住坐游禮到沙州山寺梁師父楊師父等。”①閬州閬中縣即今四川閬中市,宋代隸屬成都府路,南距合川市約120千米。
前室南壁西段題記,刻劃,文曰:“大宋府路合州赤水縣長安鄉(xiāng)楊到 此 寺居住沙州……”②其中的合州治今四川合川市,所轄赤水縣地當合川市西北65千米赤水鄉(xiāng),同隸成都府路。所以題記中的“府路”應為“成都府路”。
二題記書寫者皆來自今四川省合川縣北或西北,其中又都出現(xiàn)“楊”姓人士,書寫位置分處北壁和南壁西段,大致對應,開首皆稱“大宋”,很可能為同行者所書。這些題記不僅不支持謝氏所主西夏說,而且可看作謝說的反證。謝氏辯論說:“這些題記的年代都是在北宋年間,很可能是西夏據(jù)有敦煌之后不久……西夏據(jù)有敦煌后,敦煌地方仍然使用正統(tǒng)年號,但這種過渡時間大約只有10年左右,其典型例證就是莫高窟第444窟,當時西夏據(jù)有敦煌已10年,但窟內(nèi)題記仍用中原王朝年號。”[5]71謝氏接受的是西夏于1036年正式統(tǒng)治敦煌之說,且不論此說是否可以立足③,單就以“大宋”題記來證明西夏窟的存在而言,在邏輯上就有些不通了。論者或可作如下辯解:西夏于1036年統(tǒng)治敦煌后,勢力尚不穩(wěn)固,故允許沙州回鶻繼續(xù)向宋朝貢,敦煌石窟中出現(xiàn)大宋年號,也是西夏統(tǒng)治力量薄弱所致。如果此說不誤,敢問西夏在敦煌統(tǒng)治尚不穩(wěn)固的初期,朝不保夕,怎會有余力和心思來修建規(guī)模如此宏大的石窟呢?論者還可繼續(xù)辯解:正是由于西夏統(tǒng)治不穩(wěn)固,所以對第464窟壁畫的重繪并未下大工夫,只是在素面上重繪而已。果若如是,那又會產(chǎn)生另外一個問題:戰(zhàn)亂期間虔誠的西夏佛教徒可以作的佛事,何以至西夏統(tǒng)治穩(wěn)固后卻不能繼續(xù),以至于半途而廢呢?不可思議。謝氏所舉證的二題記不僅不支持西夏說,而且會起到相反的作用——依常理,一般會視之為西夏未能對敦煌實施有效統(tǒng)治的佐證。
謝氏的第二個論據(jù)是第464窟壁畫具有比較典型的藏傳壁畫特點。我們知道,西夏早期佛教主要受回鶻佛教和漢傳佛教的影響④,故莫高窟、榆林窟、東千佛洞所見早期西夏壁畫不管在題材、布局、人物形象、衣冠服飾,還是在繪畫技法上,都全面繼承北宋壁畫之余緒,上與曹氏歸義軍所設地方畫院及其后的沙州回鶻洞窟相銜接,具有嚴謹?shù)膶憣嵶黠L,但構圖顯得過于程式化,經(jīng)變故事情節(jié)簡略而顯得呆板。中期以后,逐漸形成了本民族的特色,最明顯的特征就是人物形象逐漸接近黨項族的面部與體質(zhì)特點,西夏所流行的服飾在壁畫中開始出現(xiàn)。至于藏傳佛教的影響進入洞窟,藏式繪畫開始流行,已是晚期之事①。西夏與藏族盡管早有接觸,但藏傳佛教在西夏流行,則始自西夏仁宗仁孝統(tǒng)治時期(1140—1193)[11]。謝繼勝明確指出:
到12世紀末,西夏人已經(jīng)完全將藏傳繪畫與本土風格有機地融合在一起并創(chuàng)造了一種新的樣式,筆者稱之為“西夏藏傳風格”,這種風格的出現(xiàn)標志著西夏具有了可辨識特征的自己的藝術風格。
第464窟壁畫即具有比較典型的筆者所謂的西夏藏傳壁畫特點。[5]74
依上述引文,第464窟已經(jīng)具有“西夏藏傳壁畫特點”,自然為12世紀末以后之遺存,而謝氏在同文中又言:“通過對莫高窟第464窟游人題記年代的分析確認該窟壁畫繪于西夏前期。”[5]79到底該窟壁畫屬于前期還是屬于后期呢?顯然自相抵牾。
謝氏確認第464窟為西夏窟之第三個證據(jù)為后室南壁所繪上師所戴帽子為寧瑪派的蓮花帽(圖版1),此為其立論的最根本依據(jù)。除該窟外,這種帽子在莫高窟第465窟、榆林窟第29窟均有出現(xiàn),幾乎完全一致。榆林窟第19窟甬道北壁有漢文刻劃題記:“乾祐十四年日甘州住戶高崇德小名那征到此畫秘密堂記。”②乾祐二十四年,即1193年,而“秘密堂”則為人們對以藏密佛窟或佛寺的一種稱謂。第19窟題記所謂“秘密堂”,據(jù)推測即榆林窟第29窟。如果此說不誤,那么榆林窟第29窟的營建年代即應在夏仁宗乾祐二十四年(1193)[12]。另外,在酒泉文殊山萬佛洞、瓜州東千佛洞第4窟、千佛洞第7窟、寧夏山嘴溝石窟、寧夏拜寺口西塔、黑水城出土唐卡等西夏上師像中,也可以看到這種蓮花帽。但是,這種蓮花帽并非西夏所特有,原本為8世紀入藏的印度佛教大師蓮花生所戴之冠,后演變?yōu)椴貍鞣鸾虒幀斉傻膫鹘y(tǒng)著裝[13],誠如謝繼勝先生所言,“西夏以后的作品也同樣出現(xiàn)著蓮花冠的上師像”[5]76,不僅元明清代有所見,甚至出現(xiàn)于16世紀尼泊爾的繪畫中,直到今天,寧瑪派上師仍佩戴這一形式的蓮花帽。故這種著蓮花帽上師像的出現(xiàn),不足以支撐西夏說的成立。
第464窟被定為西夏窟的第四個證據(jù)是后室窟頂藻井的大日如來像。該窟窟頂繪五方佛,東西南北四披四位如來均為漢地繪畫風格,但中央的大日如來卻為藏傳繪畫風格(圖版2)。這種畫法在西夏繪畫中極為多見,但不可否認的是,在藏傳佛教藝術中,這種畫法一直盛行不衰,非西夏所特有,同樣不足以證明西夏說的成立。
第464窟之所以被定為西夏窟,還有一個潛在的理由,即該窟有多處西夏文題記。據(jù)有關人員調(diào)查,窟中現(xiàn)存西夏文題記7則,其中5則用硬物刻劃,二則用粗筆墨寫[14]。一般而言,硬物刻劃文字不可能出自石窟創(chuàng)建者之手,而是后來朝山者的隨意題寫。二則墨書題記,都很簡單,總共只有5個字,顯然亦非創(chuàng)建者所書。正如刊布者所言,以上7則題記均為“巡禮題款”。這些題記多書寫于前室南北壁的西端素壁上,與前述“大宋”漢文題記并書,后均為加長的甬道所覆蓋。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后室東壁甬道頂部書有梵文六字真言(圖4),讀作:O mani padme hūm(唵嘛尼把密吽,又見于前室南北二壁),與壁畫渾然一體,屬于同一時代之物。它的存在直接否定了西夏說。
在藏傳佛教中,六字真言(六字大明咒)又被稱作觀世音菩薩的大悲心咒,只要常念這神奇的咒語,即可獲得現(xiàn)報,修持方法極簡單易行。14世紀成書的《王統(tǒng)記(Gyalrab Salwai Melong)》以《白蓮花經(jīng)》①的基本思想為基礎,對六字真言所體現(xiàn)的觀音法力作了如是概括:
此六字咒,攝諸佛密意為其體性,攝八萬四千法門為其心髓,攝五部如來及諸秘密主心咒之每一字為其總持陀羅尼。此咒是一切福善功德之本源,一切利樂悉地之基礎。即此便是上界生及大解脫道也。[15]
作者把這六個神奇的字與佛教的“六道”理論結合了起來,認為六字與“六道”有著密切的對應關系:
“唵”,除天道生死之苦;“嘛”,除阿修羅道斗諍之苦;“呢”,除人道生老病死之苦;“叭”,除畜生道勞役之苦;“咪”,除餓鬼道饑渴之苦;“吽”,除地獄道寒熱之苦。[15]21
這樣,六字真言也就差不多成了佛法的象征,幾乎涵蓋了佛教的眾多精義。這種解釋雖有點背離梵文的原始意義,但極大地神化了六字真言的不凡法力,而且將六字與“六道”巧妙地附會在一起,更容易為信徒所理解和接受,從而對六字真言的信受奉行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除了信眾之外,這一說法也得到了學界的普遍認可②。
六字真言在吐蕃中出現(xiàn)的最早證據(jù),可追溯到吐蕃占領敦煌時期(786—848)。在那個時代書寫的古藏文文獻中,即已發(fā)現(xiàn)有用吐蕃文書寫六字真言的情況,如倫敦印度事務部圖書館藏S.T.420-1、S.T.421-1、S.T.720[16]及巴黎法國國立圖書館藏P.T.37、P.T.51等藏文寫卷即是[17]。這些寫卷盡管有的已很殘破,而且寫法也不無差異,但都以無可辯駁的事實表明,至遲在8—9世紀時,六字真言在吐蕃中即已出現(xiàn)了。此后,隨著藏傳佛教在后弘期的迅猛發(fā)展,六字真言也開始逐步流行起來,至于在全國范圍內(nèi)的廣泛傳播,則應自元朝始[18]。
就西夏而言,在為數(shù)眾多的藏傳佛教畫品中,六字真言迄今尚無所見,榆林窟第29窟為西夏窟,窟頂藻井井心有墨書梵文六字真言,但為元代之遺墨[19]。說明那個時代六字真言在西夏尚不流行。而第464窟之梵文六字真言與壁畫作于同時,則該窟非西夏窟可明矣。
綜合以上各因素,足證西夏說是缺乏根據(jù)的,難以成立③。
三 原窟為北涼禪窟
那么,第464窟應創(chuàng)建于何時呢?近期的考古資料有助于解決這一問題。考古資料證明,第464窟原為多室禪窟,前室(即原來的主室)南北二壁原各開兩個小禪窟(圖5)[2]54-56。
眾所周知,莫高窟禪窟的開鑿主要在隋代以前,隋以后開窟雖多,但均為功德窟,未見到一所禪窟。
莫高窟現(xiàn)存洞窟中,最早的禪窟為第268窟。敦煌研究院過去將第268窟主室南北側壁的四個小龕分別編為第267、269、270、271窟(圖6)。從整個洞窟結構看,四個小龕均屬第268窟之組成部分,故應視作一個窟來看待。這四個小龕面積很小,“才容膝頭”⑤,是禪室無疑。全窟僅正壁及窟頂有造像,側壁及兩側禪室皆無造像,整體窟室結構保留了西北印度地區(qū)禪窟與設像處所分離的原則①。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從第270窟暴露出來的層位關系看,這一組窟龕經(jīng)過了兩次重修,現(xiàn)存第一層是隋畫千佛(第268窟西壁未重畫),第二層是北涼時期(401—439)畫的金剛力士和飛天等,與第268窟西壁下的供養(yǎng)人屬于同層。在北涼畫下有一層白色粉壁,無畫,是證該窟原本即無壁畫,供禪僧坐禪苦修之用[20]。其開鑿時代被定為北朝第一期,即北涼統(tǒng)治敦煌時期(420—442)②。
屬于北朝第二期(即北魏時期)的禪窟有第487窟。該窟由前室和后室兩部分組成,其中前室現(xiàn)存部分呈橫長方形,從殘存遺跡看,原為面闊三間的窟檐式建筑。主室平面呈方形,中部偏西筑有方形低壇,南北二側壁各鑿出四個小禪室③。
屬于第三期(即西魏時期)的禪窟有第285窟,堪稱莫高窟禪窟中最為典型者。該窟南北二壁各營建小禪室四個(圖7),該窟北壁東起第一鋪滑黑奴造無量壽佛發(fā)愿文的紀年,可以證明第285窟完成于西魏大統(tǒng)五年(539)或稍后[21]。
上述諸窟小禪室面積都很小,不足半平方米,僅能容一人打坐,室內(nèi)亦無色彩粉飾,僅用泥輕抹而已,禪僧們面壁打坐,寓示四大皆空,無所執(zhí)著。入靜一無所求,出靜則繞佛壇念佛,故滿室飾彩壁畫,昭示著美妙的極樂世界,通過鮮明的比照使禪機得到進一步升華[22]。而窟內(nèi)壁畫中的禪定比丘列像,“并不是表現(xiàn)修行中的比丘,更大的可能性是表現(xiàn)步陟禪定修行階梯,最終獲得阿羅漢果,得到了神變的高僧神僧”[23]。
此外,與之相仿的還有新疆吐魯番吐峪溝北涼第42窟(格倫威德爾編號第4窟)。該窟窟頂呈縱劵頂,平面為長方形,后壁開一禪室,東西兩側壁各開兩禪室(圖8),內(nèi)繪比丘禪觀圖。值得注意的是,該窟縱劵頂兩側壁有三排比丘禪觀圖。所繪內(nèi)容和十六國時期流行的禪觀思想息息相關,所依禪經(jīng)主要有鳩摩羅什譯《禪秘要法經(jīng)》、《坐禪三昧經(jīng)》和《禪法要解》④。日本學者山部能宜通過圖像與經(jīng)典的比對,認為第42窟之壁畫與424年畺良耶舍譯《觀無量壽經(jīng)》最為接近,但又不盡相同,應含有中亞地方因素①。若此說成立,那么第42窟之開鑿應在424—460年之間②。
綜觀以上所列禪窟,北魏第487窟與西魏第285窟之形制基本一致,均在主室側壁各開4個小禪室,而北涼第268窟和吐峪溝同時代第42窟則更為接近,各于側壁開2個小禪室,與第464窟所見幾無二致。考慮到隋代以后未見有禪窟開鑿,故可將第464窟始造時代推定在北朝時期,若再考慮其形制特點,似定為北涼窟較為穩(wěn)妥。
北涼時期,在敦煌禪修的僧人數(shù)量應是較多的,僅有第268窟的4個小禪窟顯然不夠用,20世紀末北區(qū)的考古發(fā)掘告訴我們,莫高窟用于修禪的石窟多在北區(qū)。莫高窟北區(qū)現(xiàn)有石窟248個(含敦煌研究院編號第461—465窟)其中專供僧人修行習禪用的石窟就有82個,另有5個僧房窟附設禪窟[24]。其中,B125窟為一單禪室窟,樹輪校正年代為420年,被推定為北涼時期[25]。B113為一多禪室窟,形制與吐峪溝石窟第42窟幾乎完全一致,亦當為北涼窟[26]。說明自北涼始,莫高窟北區(qū)即為禪僧修行的集中區(qū)。
總之,可以看出第464窟最初開鑿于北涼時期,原為多室禪窟。此后長期被廢棄,及至元代,通往禪窟的甬道被封堵,多禪室窟遂演變?yōu)榕X羅窟。隨著前室的坍塌,原來的中室變成了前室[2]54-56。
四 出土文獻及相關問題
自20世紀初以來,第464窟出土了大量不同文字的文獻。在敦煌莫高窟所有洞窟中,除藏經(jīng)洞之外,以該窟出土文獻最多,故有“第二藏經(jīng)洞”之稱[27]。1908年,法國探險家伯希和曾造訪該窟,將其編為181窟,并于洞中清理出不少文獻,約有600件左右。他在筆記中寫道:
那里也有漢文、藏文、婆羅謎文和蒙古文的殘卷,同時也有一些西夏文刊本短篇殘書。這是一種新奇事。我讓人完成了對洞子的清理,大家于那里最終發(fā)現(xiàn)了相當數(shù)量的印有西夏文的紙頁,他們至少屬于4部不同的書籍。[28]
繼伯希和之后,張大千先生于1941—1943年進駐敦煌,逗留莫高窟期間,曾對北區(qū)部分洞窟進行了非科學性挖掘,獲得回鶻文、西夏文、漢文、蒙文等文書百余件,原為張大千個人收藏,后攜往域外,其中相當一部分現(xiàn)收藏于日本天理大學附屬天理圖書館,構成了該館收藏敦煌文獻的主體[29]。如編號為180-ィ1“敦煌遺片”一冊共8葉,其內(nèi)收有西夏文、藏文、回鶻文和漢文佛典寫本或刻本斷片;編號222-ィ63則為“西夏、回鶻文書斷簡”一冊,共18葉,其中主要是回鶻文文獻;編號183-ィ279為“西夏文斷簡”一冊,有近百文書整葉和殘片,經(jīng)張大千先生重裱成44葉。在日本藤井有鄰館和瑞典國立民族學博物館中,也有一些來自敦煌,但并非出自莫高窟藏經(jīng)洞(第17窟)的回鶻文文獻。據(jù)研究,這些文獻大多都應出自莫高窟第464窟③。1989年敦煌研究院考古人員對該窟進行了系統(tǒng)發(fā)掘,又獲得了90余件古代文獻。
第464窟出土文獻經(jīng)過整理研究,今已大體明確,以印本居多,大多屬元代之物。
前人多言,前室有雙層壁畫,底層為西夏畫,外層為元畫。筆者仔細觀察,卻看不出哪個地方有重層壁畫之遺痕。該窟內(nèi)容復雜,為清楚起見,這里將其分作三個層面來敘述。
其一為第464窟之原始形態(tài),建于北涼,為禪窟。但有無繪畫已看不出,從現(xiàn)存壁面觀察,當時無畫,應為素壁。
其二為后室,北、西、南三壁前設佛床,但塑像今已蕩然無存,唯壁畫保存完好,具有顯密融合的藝術特點,明顯受到藏傳佛教的影響。
其三為前室與甬道。后室甬道原來僅為0.90米左右,后來向東加長為2.50米,在西南角和西北角各構成一個封閉式方室,然后繪制壁畫。從畫面看,甬道二壁、甬道加長部分二側壁與前室南北壁壁畫是渾然一體的,不管是線條、著色還是暈染法以及前室窟頂與甬道頂部所保存的千佛造像,都是完全一致的,無疑完成于同時。
加長甬道以構成獨立的小方室,這種情況在莫高窟極其罕見。何以如此?值得深究。
眾所周知,二方室之內(nèi)各圍一廢棄的小禪室,其中西北角的小禪室后來成為瘞埋“元代公主”之墓(圖5)。1920年,滯留于莫高窟的沙俄殘部,曾對該墓進行了盜掘,將其中的珠飾釵鈿洗劫一空[47]。唯留一只“公主”腳,至今尚存于敦煌研究院[48]。至于“元代公主”之由來,史無明載。在莫高窟北區(qū),用于瘞埋僧人骨灰、遺體和遺骨的瘞窟有25個,其中15個是專門為瘞埋死者而開鑿的瘞窟,另有7個窟是改造原來的禪窟而成[24]346-347。第464窟“公主墓”顯然屬于后者,但值得注意的一點是,第464窟規(guī)模與通常的瘞窟是不可相提并論的,若沒有特殊且尊貴的地位,是不可能獲此殊榮的,尤其是當時為了掩人耳目,竟對石窟整體結構進行了改造,將原來的甬道加長一倍以上,將公主墓完全隱藏了起來。由是以觀,“元代公主”墓之說當非空穴來風,而是可信的。公主身份高貴,隨葬物較多可想而知。為保持一致,在石窟前室西南角也修建了同樣形狀的方室。
1908年,伯希和對第464窟進行了考察,并予以清理,獲得眾多文物。關于該窟的內(nèi)容與時代,他作了如下敘述:
過道中每個壁面的裝飾主要由占據(jù)了洞窟整個上部的一幅畫組成,它約有3米長,位于a、b之間,被分成由冗長的蒙文引文分隔開的斜長的小畫面,而這些引文一般均寫作紅色,唯有引文開始處得標題系用藍色寫成,所有的題識都寫于黑色底面上。這一切絕會使人產(chǎn)生一種印象,認為它們原來是組成長篇蒙文和藏文寫本的葉子,而那些繪畫則相當于在內(nèi)部裝飾了夾板的兩個版面的細密畫。有關這種裝飾(它也是過道中和洞子中的裝飾)的時代,我們掌握有如下論據(jù):它覆蓋了一個石灰粉刷層,后者上面就寫滿了西夏文(同時還有藏文和漢文)游人題記。因此,它肯定是元代的。[28]374
伯氏依石窟中的蒙古文題記,且題記書寫于壁畫營造之初,從而確定該窟為元代之物。這一斷代是可信的,但必須指明一點,其中的文字為回鶻文而非蒙古文。伯希和精通回鶻文,可能是時間緊迫,加上題記多模糊不清,導致伯希和作出了錯誤的判斷,但這一誤判并不動搖其斷代的根基。
伯氏依題記對石窟的斷代之法為日本學者森安孝夫所接受,他進一步引申說:
由伯希和圖錄觀之,第181窟壁面上的回鶻文,并沒有后世不斷添加或涂鴉的痕跡,而是在營造之初與壁畫同時寫上去的。這是不會錯的。有一藏文題銘,觀其與壁畫之關系,倒可定為后世添加物。故而,若將第181窟定于西夏時期(并非開鑿),那窟中會存在與壁畫相一致的回鶻文榜題也就匪夷所思了。所以,還應遵從伯希和的推斷,認為是在“蒙古統(tǒng)治時期”的看法是妥當?shù)摹49]
應該說,森安的思考也是有根有據(jù)的,遺憾的是,他并未意識到第464窟的壁畫是雙層的,表層為元代,本無異議,但還有底層壁畫。森安為肯定該窟為回鶻窟,為否認西夏因素的存在而斷定第464窟出土的西夏文文獻也為蒙元時代回鶻人使用之物[50]。似乎大可不必。關鍵還在于窟中的題記,如伯氏所說,這些題記與壁畫形成于同一時間,故題記的釋讀對壁畫的斷代與定性勢必會產(chǎn)生決定性的影響。
上文釋讀的三則題記,反映的是四地、五地和十地菩薩,九地菩薩雖榜題毀失,但圖像猶在。《法門名義集》云:“圣種性有十地菩薩,自此已后是出間圣人之位。”[40]202從窟中現(xiàn)存遺跡可以看出,甬道二壁所繪恰為十尊菩薩,合為“十地菩薩”,除現(xiàn)存4尊外,其余6尊皆因土坯所砌甬道的被毀而殘缺,如北壁甬道現(xiàn)存部分呈曲尺形,下邊長2.50米,上邊殘長0.90米(圖版8),就是明顯的例證。
其中,一至五地菩薩位于南壁,自左向右依次排列;六至十地菩薩位于北壁,自右向左依次排列。從1908年伯希和所攝照片看,西北角和西南角的兩個方室當時即已被拆毀[50],原作為方室建筑一部分的甬道南北二壁延伸墻壁上的菩薩像也隨之毀于一旦。
依據(jù)甬道十地菩薩榜題,結合窟內(nèi)隨處可見的其他回鶻文題記,勢必需將之與回鶻相聯(lián)系。考慮到前室二壁中的四體六字真言和五體六字真言的存在,加上洞窟中出土的文獻絕大多數(shù)為元代之物,可以認為,第464窟前室及甬道現(xiàn)存壁畫應出自回鶻之手,為元代之畫作。而元代也是回鶻在敦煌比較活躍的時期。
至于畫風問題,因本人對石窟藝術素無研究,故特向敦煌研究院西夏、回鶻壁畫研究專家劉玉權先生求教。劉先生言:第464窟壁畫明顯不屬于西夏,而有回鶻畫風特點,但由于與他辨識出的23座沙州回鶻洞窟差別甚大,故在分期排年時,將第464窟排除在沙州回鶻窟之外。劉玉權當時確認的沙州回鶻洞窟計有23座,分為前后二期,茲引錄如表1:
其中第237窟(張編53窟)、309窟(張編98窟)和310窟(張編99窟),早在20世紀40年代即已被張大千確定為回鶻窟[3]124-126,222-224。另外,莫高窟第368窟(張編172窟)也曾被張大千確定為回鶻窟[3]250-251,但在劉玉權的分期排年中卻被排除在外。劉先生所列第23窟,其時代應在11世紀70年代以前,這時的回鶻完全受漢傳佛教的影響,堪稱漢傳佛教在西域的翻版[52],而第464窟壁畫卻不同,后室明顯受到了藏傳佛教的影響,前室與甬道繪畫盡管以漢風為主,無明顯藏傳佛教繪畫特點,但與上述所列第23窟繪畫之畫風亦迥然有別,乃時代變遷與文化變異所帶來的必然結果。看來,張大千將第464窟定為“回鶻修”當是頗有見地的。除壁畫外,張氏所作結論似乎還肇基于該窟內(nèi)西夏文、回鶻文題記之眾多。前文已指出“西夏說”之非,此不贅述。但其中的回鶻文題記當是與壁畫同時共生的,非后人所題寫,這一點是不容懷疑的。就這一點言,張氏的結論是頗有見地的。
這里還存在另外一個問題,敦煌偏處西北,何來“元代公主”之葬呢?恐還需從瓜沙地區(qū)的統(tǒng)治者——蒙古豳王家族與敦煌石窟的關系中尋找答案。
眾所周知,蒙古于1227年占領敦煌,“隸八都大王”[53]。元世祖至元十四年(1277),元政府設瓜沙二州,隸肅州,歸中央政府管轄,授當?shù)匕傩仗锓N、農(nóng)具。十七年,沙州升格為路,設總管府,統(tǒng)瓜沙二州,直接隸屬于甘肅行中書省。十八年正月,“命肅州、沙州、瓜州置立屯田”[54]。是后于至元二十四年始筑沙州城,“以河西愛牙赤所部屯田軍同沙州居民修城河西瓜、沙等處。”[55]4年后,以政局不穩(wěn),元政府盡徙瓜州居民入肅州,瓜州名存實亡。這一時期,瓜沙之地位漸趨衰微,直到大德七年(1303)隨著蒙古大軍的屯駐,局面才得以扭轉。《元史》卷21載:
[大德七年]六月己丑,御史臺臣言:“瓜、沙二州,自昔為邊鎮(zhèn)重地,今大軍屯駐甘州,使官民反居邊外,非宜。乞以蒙古軍萬人分鎮(zhèn)險隘,立屯田以供軍實,為便。”從之。[56]
是時,“甘州軍隸諸王出伯”[57]。出伯與其弟哈班均受賜金印,以諸王身份出任河西至塔里木南道方面軍事統(tǒng)帥重任,節(jié)制甘肅行省諸軍。大德八年,“封諸王出伯為威武西寧王,賜金印”[59]461。蒙古崛起朔漠,肇興之初各種制度尚不完善,因此諸王初無位號,僅有六等印紐的賜予,中統(tǒng)以后才開始以國邑之名封號,但仍以六種印紐分等[58]。威武西寧王位列諸王第三等,佩金印駝紐。大德十一年,出伯進封豳王[59],由三等諸王晉升為一等,佩金印獸紐,由甘州移駐肅州(今甘肅酒泉市),豳王烏魯斯得以正式形成。接著,天歷二年(1329)出伯子忽答里迷失(又作忽塔迷失、忽答的迷失、忽塔忒迷失)被封為西寧王,佩金印螭紐,位列二等諸王,駐于沙州(甘肅省敦煌市)。是年十二月,忽答里迷失進封豳王。[60]翌年,西寧王之位由其侄速來蠻繼襲①。元統(tǒng)二年(1334)五月,又以出伯子亦里黑赤襲其舊封為威武西寧王[61],地位次于西寧王,佩金印駝紐,駐于新疆哈密。出伯兄哈班之后寬徹于天歷二年八月被封為肅王[60]739,位同豳王,為一等諸王,佩金印獸紐,駐于瓜州(甘肅省瓜州縣)[62]。本文所謂的豳王家族即為豳王、西寧王、威武西寧王和肅王的總稱。有元一代,豳王家族受元政府之名統(tǒng)領鎮(zhèn)戍諸軍,防守西起吐魯番東至吐蕃一線。
蒙古大軍入駐后,瓜沙社會生產(chǎn)逐步得到恢復發(fā)展,莫高窟、榆林窟的佛事活動也在元代晚期漸趨高漲。至順二年(1331)瓜州知府、瓜州郎使郭承直與其子郭再思、司吏吳才敏、巡檢杜鼎臣等巡禮榆林窟,是元代最早的紀年題記②。西寧王速來蠻鎮(zhèn)守沙州,于至正八年(1348)在莫高窟立《六字真言碣》,率領王子、王妃、公主、駙馬等誦經(jīng)奉佛[63]。三年后,速來蠻又主持修復莫高窟文殊洞(第61窟)外的皇慶寺[63]112-116。在莫高窟現(xiàn)存的10個元代石窟(第1、2、3、95、149、462、463、464、465、477窟)中,大多都屬于晚期。至正十三年,守鎮(zhèn)官員下令重修榆林窟③。榆林窟的4個元窟(第3、4、6、27窟),都建于元代晚期。
由于蒙古統(tǒng)治者如同西夏晚期統(tǒng)治者一樣推崇藏傳佛教,自西夏以來即流行于敦煌的藏傳佛教得以繼續(xù)發(fā)揚光大,故莫高窟現(xiàn)存的藏傳佛教藝術除去西夏傳下來的漢密畫派(如第3窟和61窟甬道)之外,又有風格迥異的金剛乘藏密畫派(如第465窟)[64]。在莫高窟、榆林窟現(xiàn)存14個元代洞窟中,又以屬于晚期者居多[65],故學界認為“元代晚期方是莫高、榆林二窟修建的高漲時期”[66]。這種局面的形成,蓋與瓜沙地區(qū)統(tǒng)治者豳王家族在敦煌大興佛事有關。對此,筆者擬另文詳述,茲不復贅。前文述及的“元代公主”,很可能就是豳王家族成員之一。如同莫高窟《六字真言碣》所顯示的那樣,豳王家族成員有王子、王妃、公主、駙馬等,稱號幾同于中原大汗。說明諸王之女也被稱作公主[63]108-112。曾出家為尼的某公主,亡后瘞埋于第464窟。否則,敦煌何來公主呢?而亡于他地,并未在敦煌出過家的中原大汗之女絕不會千里迢迢而遠葬西北邊陲之地敦煌。
有元一代,回鶻與蒙古王室關系密切,回鶻亦都護巴而術阿而忒的斤被成吉思汗封為第五子,享受諸王待遇,并嫁公主[67]。是后,回鶻人中大凡“有一材一藝者畢效于朝”[68]。豳王家族“兼領瓜沙以西北至合剌火者畏兀兒地征戍事”[69],與回鶻關系同樣非常密切,故酒泉文殊山石窟發(fā)現(xiàn)的著名碑刻——漢—回鶻文合璧《重修文殊寺碑》記錄了豳王家族興修文殊寺的事跡,碑主為第三代豳王喃答失太子[70]。作為蒙古人,碑文不用蒙古文,卻使用漢文與回鶻文。至正十二年(1352),來自哈密的威武西寧王不顏嵬厘赴榆林窟朝山,題寫的文字也是回鶻文而非蒙古文,均體現(xiàn)了回鶻與豳王家族關系之特殊性。前已述及,第464窟出土文獻差不多均為元代之物,凡紀年明確者,皆屬14世紀的早期和中期,其中Or.8212-109回鶻文《吉祥勝樂輪》甚至是奉沙州西寧王子阿速歹(Asuday)之命而抄寫的[71]。在北京大學圖書館收藏的敦煌寫本(北大D154V和北大附C29V[72])中還有兩首贊美西寧王速來蠻的回鶻文頭韻詩,證實當?shù)鼗佞X佛教與豳王家族間存在著極為密切的關系[73]。其出土地點雖不詳,但依早期發(fā)現(xiàn)元代回鶻文文獻的情況看,應以第464窟可能性最大。
其時當在元朝的后半,正值莫高窟營建之高漲期。第464窟由回鶻修復,窟內(nèi)卻瘞埋著蒙古豳王家族的公主,那么,回鶻之修復活動則必與豳王家族息息相關。易言之,豳王家族應為該窟的供養(yǎng)主。
有一個現(xiàn)象特別值得注意,后室東壁即甬道西口南北二側壁之壁畫在保存完好而且非常清晰的情況下曾被人粉刷過,覆蓋后題以回鶻文文字(圖版9)。其中,南側滿壁書文字29行,北側第1行文字未及寫完便戛然止筆了,顯然系受外力影響而中斷。何以如此?令人費解,或許只有那些已完全模糊不清的回鶻文文字能夠告訴我們原因,遺憾的是這些文字今天已完全無法辨識了。筆者個人臆測,應為功德記之屬,期待著來日能有辦法釋讀出這些文字,為疑團的解決提供些許信息。
在敦煌石窟營建過程中,未竣工而突然終止的情況時有所見,尤其是在北朝、五代等戰(zhàn)亂年代更是常見。致其生變的因素固然很多,但改朝換代始終居于首位,第464窟之情況當亦屬同樣因素所致。
至正二十八年(1368),朱元璋建立明朝,并于同年攻陷元都大都,元朝滅亡,但瓜沙二州尚處于蒙古豳王家族統(tǒng)治之下,第464窟前室南壁東段墨書“至正卅年(1370)五月五日”[74]即是明證,因為至正二十八年元朝即已滅亡了,但瓜沙地區(qū)仍行用元朝年號。洪武五年(1372),朱元璋遣馮勝率大軍經(jīng)略河西,在瓜沙擊敗元朝留守河西軍之殘部。第464窟之修復活動之所以功未竟而突然中止,當與這場變故有關。能夠對我們這一解釋提供佐證的是第464窟大批回鶻文木活字實物的發(fā)現(xiàn)。1908年,伯希和于此窟掘獲回鶻文木活字968枚,1989年,敦煌研究院考古人員又發(fā)現(xiàn)19枚。這些活字,都為蒙元時代之物①,敦煌回鶻掌握并開始使用活字印刷的時間,似乎應在12世紀末到13世紀上半葉[75]。第464窟廢棄活字之時代,伯希和推定為1300年左右[76]。這些說明該窟在元代時有可能是一個回鶻刊經(jīng)場所[28]375。在經(jīng)歷數(shù)百年之后,在同一窟中尚能發(fā)現(xiàn)如此眾多的木活字實物,說明當時活字印刷的廢棄應是短時間內(nèi)發(fā)生的;反之,如果是逐步廢棄的,那么活字實物就會自然散亂,而不可能呈現(xiàn)如此集中的狀態(tài)。
第464窟前室與甬道壁畫為同時所繪,但后室明顯與之不同,除了線條、著色迥異外,前室所用暈染法,在后室完全看不到,甬道菩薩造像所用瀝粉堆金法,在后室也是看不到的。就繪畫風格論,前室所見善財五十三參變與后室所見觀音三十二應化現(xiàn)變也迥然有別,前者揮毫恣意,大度有力,瀟灑疏朗,頗有大家風范;后者工筆嚴謹,精致細膩,內(nèi)涵豐富,呈細密之風[1]23。這些都說明,二者非同一時代所畫。前文已論及,后室東壁有梵文六字真言,說明該窟的上限不早于元初。值得注意的是,該窟東壁甬道二側之畫面曾被粉刷過,并覆以回鶻文題記。從壁面的疊壓關系,明顯可以看出,前室要晚于后室。結合各種因素,可定后室壁畫當為元代早期之遺存,其壁畫少部分遭到破壞之事,當發(fā)生在元朝末期。當時回鶻所覆蓋的畫面尚相當清新,證明二者時代相距不遠,推定為百年以內(nèi)當不致大誤。
這些因素說明,第464窟前室與甬道是回鶻人在蒙古豳王家族的支持下進行修復的,確切地說,具體時間當在元朝末期,但不遲于《吉祥勝樂輪》的抄寫年代——1350年。在甬道與前室完工后,回鶻人有意保留了當時保存尚完好的后室,僅對后室東壁甬道二側的墻壁進行了粉刷,準備題寫文字。由于明朝軍隊突然攻破沙州,文字的題寫工作尚未完畢便草草收場了,該窟遂再度廢棄。
七 結 論
綜上所述,可以得出如下結論:莫高窟第464窟的開鑿是在北涼而非目前流行的說法西夏;原為多禪室窟,后來(很有可能為元代)通往南北二壁的禪窟甬道被封堵,多禪室窟變成了毗訶羅窟;由于前室坍塌,原來前室、中室(主室)、后室形制變?yōu)榍笆液秃笫医Y構;后來,回鶻在蒙古豳王家族,即沙州西寧王的支持下重修洞窟,并加長了原來通往后室的甬道,構成方室以掩蓋方室內(nèi)側的元代公主墓,并根據(jù)勝光法師譯回鶻文本《金光明最勝王經(jīng)》在甬道南北二壁繪制了十地菩薩像,窟內(nèi)隨處可見回鶻文題記,可確認前室與甬道現(xiàn)存壁畫當出自回鶻之手,窟內(nèi)有藏傳佛教風格的六字真言題辭二方,加上洞窟內(nèi)發(fā)現(xiàn)的古代文獻、文物絕大多數(shù)均屬元代末期,故而可確認該窟前室與甬道為元代回鶻窟,更確切地說,應為元末的洞窟。后室則為元代早期洞窟。
與第464窟毗鄰的第465窟和第463窟,繪畫風格也與其十分近似,故學界通常將以上三窟定為同一或相近時代之物①。那么,第465、463窟是否也如森安孝夫所推想的那樣,“是回鶻佛教徒開鑿的”②呢?有待學界進一步研究。
參考文獻:
[1]梁尉英.元代早期顯密融匯的藝術——莫高窟第四諸窟的內(nèi)容和藝術特色[M]//敦煌研究院,江蘇美術出版社,編.敦煌石窟藝術·莫高窟第四、三、九五、一九四窟(元).南京:江蘇美術出版社,1997:11.
[2]彭金章,王建軍.敦煌莫高窟北區(qū)石窟:第3卷[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54,62,65.
[3]張大千.莫高窟記[M].臺北:故宮博物院,1985:628-629.
[4]照那斯圖,楊耐思.八思巴字研究[G]//中國民族古文字研究會.中國民族古文字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374-392.
[5]謝繼勝.莫高窟第465窟壁畫繪于西夏考[J].中國藏學,2003(2):69-79.
[6]劉玉權.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西夏洞窟分期[G]//敦煌研究文集.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82:273-318.
[7]劉玉權.敦煌西夏洞窟分期再議[J].敦煌研究,1998(3):1-4.
[8]關友惠.敦煌宋西夏石窟壁畫裝飾風格及其相關的問題[C]//2004年石窟研究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1111-1141.
[9]梁尉英.莫高窟第464窟善財五十三參變[J].敦煌研究,1996(3):43.
[10]王惠民.敦煌西夏洞窟分期及存在的問題[J].西夏研究,2011(1):64.
[11]史金波.西夏的藏傳佛教[J].中國藏學,2002(1):35-37.
[12]劉玉權.榆林窟第29窟窟主及其營建年代考論[C]//段文杰敦煌研究五十年紀念文集.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1996:130-138.
[13]謝繼勝.西夏藏傳繪畫——黑水城出土西夏唐卡研究[M].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173-174.
[14]史金波,白濱.莫高窟、榆林窟西夏文題記研究[J].考古學報,1982(3):377.
[15]索南堅贊.王統(tǒng)記[M].劉立千,譯.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20.
[16]L. de la Vallee Poussin.Catalogue of the Tibetan Manuscripts from Tun-huang in the India Office Library[M].Oxford University, 1962.
[17]王堯,主編.法藏敦煌藏文文獻解題目錄[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7,10.
[18]楊富學.浚縣大伾山六字真言題刻研究[G]//大伾文化(一).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183-184.
[19]霍熙亮,編.榆林窟、西千佛洞內(nèi)容總錄[M]//中國石窟·安西榆林窟.北京:文物出版社,東京:平凡社,1997:260.
[20]賀世哲.敦煌莫高窟北朝石窟與禪觀[J].敦煌學輯刊:第1集,1980:43.
[21]樊錦詩,馬世長,關友惠.敦煌莫高窟北朝洞窟的分期[M]//中國石窟·敦煌莫高窟:第1卷.北京:文物出版社,東京:平凡社,1981:192.
[22]王書慶,楊富學.敦煌莫高窟禪窟的歷史變遷[G]//中國禪學:第4卷.北京:中華書局,2006:314.
[23]須藤弘敏.禪定比丘圖像與敦煌285窟[C]//陳家紫,譯.1987年敦煌石窟研究國際討論會文集·石窟考古編.沈陽:遼寧美術出版社,1990:406.
[24]彭金章,王建軍.敦煌莫高窟北區(qū)石窟:第1卷[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343,346.
[25]彭金章,王建軍.敦煌莫高窟北區(qū)石窟:第2卷[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165.
[26]賀世哲.敦煌圖像研究·十六國北朝卷[M].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2006:12-13.
[27]劉永增.回鶻寫本與敦煌莫高窟第二藏經(jīng)洞[J].敦煌研究,1988(4):40-44.
[28]伯希和.伯希和敦煌石窟筆記[M].耿昇,譯.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7:375.
[29]王三慶.日本天理大學天理圖書館典藏之敦煌寫卷[C]//第二屆敦煌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漢學研究中心,1991:79-98.
[30]James Hamilton. On the Dating of the Old Turkish Manuscripts from Tun-huang[C]//Turfan Khotan und Dunhuang, Vortr ge der "Annemarie v. Gabain und die Turfanforshung", veranstaltet von der Berlin-Branchenburg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in Berlin (9.-12. 12. 1994). Berlin: Adademie Verlag, 1996:135-145.
[31]莊垣內(nèi)正弘.ウィグル語寫本·大英博物館藏Or.8212-109について[J].東洋學報:第56卷1期,1974:44-57.
[32]羽田亨.回鶻譯本安慧の俱舍論實義疏[G]//羽田博士史學論文集:下卷.京都:同朋舍,1975:165.
[33]薩仁高娃,楊富學.敦煌本回鶻文《阿毗達磨俱舍論實義疏》研究[J].敦煌研究,2010(1):117-124.
[34]Georg Kara. Petites inscriptions ouigoures de Touen-houang, Gy. Kaldy-nagy (ed.), Hungaro-Turcica[J]. Studies in Honour of Julius Németh, Budapest, 1976:55.
[35]G. Clauson. An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Pre-Thirteenth-Century Turkish[M]. Oxford, 1972:456.
[36]麻赫穆德·喀什噶里.突厥語大詞典:第1卷[M].校仲彝,等,譯.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418.
[37]Jens Wilkens. Das Buch von der Sündentilgung. Teil 1-2, Edition des alttürkischen K anti k1lγuluq Nom Bitig (=BBT XXV)[M]. Brepols, 2007:68.
[38]中村元.佛教語大辭典[M].東京:東京書籍,1981:1186.
[39]C.Kaya. Uygurca Altun Yaruk Giriγ,Metinve Dizin[M].Ankara,1994:194.
[40]李師政.法門名義集[M]//大正藏:第54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202b.
[41]ジヤツク·ジェス.新出の二大畫幅「華嚴經(jīng)變相七處九會おょび「華嚴經(jīng)十地品變相七處九會にっぃて[G]//尾本圭子,譯.ジヤン·フランソヮ·ヤリジヱ,監(jiān)修,秋山光和,編集.西域美術·ギメ美術館ペリオ·コレクシヨン(Les Arts de L'Asie Centrale. Collection Pelliot du Musée Guimet:Ⅰ.東京:講談社,1994:56-62.
[42]大正藏:第16冊[M].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419b-c.
[43]F. W. K. Müller. Uigurica[M]. Berlin: Abhandlungen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1908:13-14.
[44]S. Ch. Raschmann. Alttürkische Handschriften. Teil 5: Berliner Fragmente des Goldglanz-Sūtras. Teil 1: Vorworte und Erstes bis Drittes Buch[M]. Stuttgart, 2000.
[45]S. Ch. Raschmann. Alttürkische Handschriften. Teil 6: Berliner Fragmente des Goldglanz-Sūtras. Teil 2: Viertes und Fünftes Buch[M]. Stuttgart, 2002.
[46]C. Kaya, Uygurca Altun Yaruk Giri , Metin ve Dizin[M]. Ankara, 1994:194.
[47]史葦湘.絲綢之路上的敦煌與莫高窟[G]//敦煌研究文集.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82:105.
[48]劉永增.回鶻寫本與敦煌莫高窟第二藏經(jīng)洞[J].敦煌研究,1988(4):44.
[49]森安孝夫.ウィグル語文獻[M]//山口瑞鳳,編.講座敦煌(6).敦煌胡語文獻.東京:大東出版社,1985:74.
[50]Mision Pelliot en Asie Centrale, 1. Les Grottes de Touen-houang, Tome 6[M]. Paris: Libairie Paul Geuthner, 1924: 345.
[51]劉玉權.關于沙州回鶻洞窟的劃分[C]//1987年敦煌石窟研究國際學術討論會文文集·石窟考古編.沈陽:遼寧美術出版社,1990:24.
[52]楊富學.回鶻文獻與回鶻文化[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375-402.
[53]宋濂,等.元史:卷60[M].北京:中華書局,1976:1450.
[54]宋濂,等.元史:卷100[M].北京:中華書局,1976:2569.
[55]宋濂,等.元史:卷14[M].北京:中華書局,1976:299.
[56]宋濂,等.元史:卷21[M].北京:中華書局,1976:452.
[57]宋濂,等.元史:卷20[M].北京:中華書局,1976:443.
[58]杉山正明.豳王チュベィとその系譜——元明史料と『ムィッズル-ァンサブの比較を通じて——[J].史林:第65卷第l號,1982:37-38.
[59]宋濂,等.元史:卷108[M].北京:中華書局,1976:2738.
[60]宋濂,等.元史:卷33[M].北京:中華書局,1976:745.
[61]宋濂,等.元史:卷38[M].北京:中華書局,1976:822.
[62]杉山正明.ふたつのチヤガタイ家[M]//小野和子,編.明清時代の政治と社會.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83:677-686.
[63]李永寧.敦煌莫高窟碑文錄及有關問題(二)[J].敦煌研究(試刊):第2期.1982:108-112.
[64]史葦湘.關于敦煌莫高窟內(nèi)容總錄[M]//敦煌文物研究所,整理.敦煌莫高窟內(nèi)容總錄[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184.
[65]段文杰.榆林窟黨項蒙古政權時期的壁畫藝術[C]//段文杰敦煌藝術論文集.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94:441.
[66]敦煌研究院,編.中國石窟·安西榆林窟[M].北京:文物出版社、東京:平凡社,1997:247.
[67]額爾登泰,烏云達賚,校勘.蒙古秘史[M].呼和浩特:內(nèi)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1029.
[68]念常.佛祖歷代通載:卷22:敕賜乞臺薩里神道碑[M]//大正藏:第49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727c.
[69]屠寄.蒙兀兒史記:卷42:出伯傳[M].北京:中國書店,1984:337.
[70]耿世民,張寶璽.元回鶻文《重修文殊寺碑》初釋[J].考古學報,1986(2):253-263.
[71]楊富學.回鶻之佛教[M].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123-124.
[72]北京大學圖書館,上海古籍出版社,編.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敦煌文獻:第2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140,316.
[73]Abuduishid Yakup, Two Alliterative Uighur Poems from Dunhuang[G]//言語學研究:第17/18號.1999: 3-4,9-10.
[74]敦煌研究院,編.敦煌莫高窟供養(yǎng)人題記[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175.